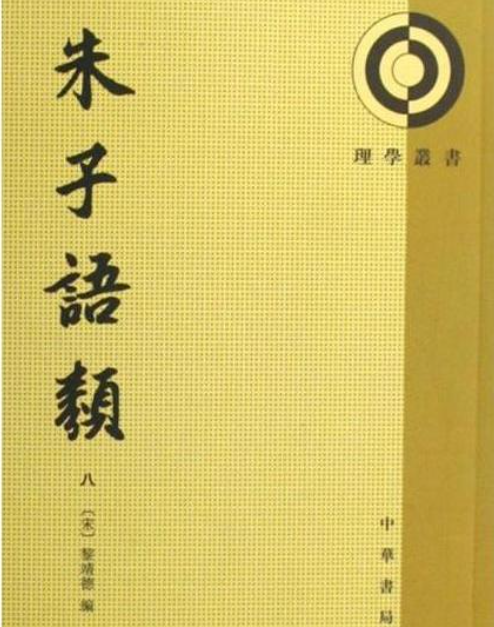中庸二
第二章
或问「君子之中庸也,君子而时中」。曰:「君子只是说个好人,时中只是说做得个恰好底事。」
问「时中」。曰:「自古来圣贤讲学,只是要寻讨这个物事。」语讫,若有所思然。他日又问,先生曰:「从来也只有六七个圣人把得定。」炎。
「君子而时中」,与易传中所谓「中重于正,正者未必中」之意同。正者且是分别个善恶,中则是恰好处。
问:「诸家所说『时中』之义,惟横渠说所以能时中者,其说得之。『时中』之义甚大,须精义入神,始得『观其会通,以行其典礼』,此方真是义理也。行其典礼而不达会通,则有时而不中者矣。君子要『多识前言往行,以蓄其德』者,以其看前言往行熟,则自能见得时中,此是穷理致知功夫。惟如此,乃能『择乎中庸』否?」曰:「此说亦是。横渠行状述其言云:『吾学既得于心,则修其辞;命辞无差,然后断事;断事无失,吾乃沛然精义入神者,豫而已矣。』他意谓须先说得分明,然后方行得分明。今人见得不明,故说得自儱侗,如何到行处分明!」
问:「『有君子之德,而又能随时以处中』,盖君子而能择善者。」曰:「有君子之德,而不能随时以处中,则不免为贤知之故有君子之德,而又能随时以处中,方是到恰好处。」又问:「然则小人而犹知忌惮,还可似得愚不肖之不及否?」曰:「小人固是愚,所为固是不肖,然毕竟大抵是不好了。其有忌惮、无忌惮,只争个大胆小胆耳。然他本领不好,犹知忌惮,则为恶犹轻得些。程先生曰:『语恶有浅深则可,谓之中庸则不可也。』以此知王肃本作『小人反中庸』为是,所以程先生亦取其说。」
问:「如何是『君子之德』与『小人之心』?」曰:「为善者君子之德,为恶者小人之心。君子而处不得中者有之,小人而不至于无忌惮者亦有之。惟其反中庸,则方是其无忌惮也。」
至之疑先生所解「有君子之德,又能随时以得中」。曰:「当看『而』字,既是君子,又要时中;既是小人,又无忌惮。」
以性情言之,谓之中和;以礼义言之,谓之中庸,其实一也。以中对和而言,则中者体,和者用,此是指已发、未发而言。以中对庸而言,则又折转来,庸是体,中是用。如伊川云「中者天下之正道,庸者天下之定理」是也。此「中」却是「时中」、「执中」之「中」。以中和对中庸而言,则中和又是体,中庸又是用。
或问子思称夫子为仲尼。曰:「古人未尝讳其字。明道尝云:『予年十四五,从周茂叔。』本朝先辈尚如此。伊川亦尝呼明道表德。如唐人尚不讳其名,杜甫诗云:『白也诗无敌。』李白诗云:『饭颗山头逢杜甫。』」
近看仪礼,见古人祭祀,皆称其祖为「伯某甫」,可以释所疑子思不字仲尼之说。灏。
第四章
问「道之不明、不行」。曰:「今人都说得差了。此正分明交互说,知者恃其见之高,而以道为不足行,此道所以不行;贤者恃其行之过,而以道为不足知,此道之所以不明。如舜之大知,则知之不过而道所以行;如回之贤,则行之不过而道所以明。」舜圣矣而好问,好察迩言,则非知者之过;执两端,用其中,则非愚者之不及。回贤矣而能择乎中庸,非贤者之过;服膺勿失,则非不肖者之不及。铢
问:「知者如何却说『不行』?贤者如何却说『不明』?」曰:「知者缘他见得过高,便不肯行,故曰『不行』;贤者资质既好,便不去讲学,故云『不明』。知如佛老皆是,贤如一种天资好人皆是。」炎。
子武问:「『道之不行也』一章,这受病处只是知有不至,所以后面说『鲜能知味』。」曰:「这个各有一般受病处。今若说『道之不明也,智者过之,愚者不及也;道之不行也,贤者过之,不肖者不及也』,恁地便说得顺。今却恁地跷说时,缘是智者过于明,他只去穷高极远后,只要见得便了,都不理会行。如佛氏之属,他便只是要见得。未见得时是恁地,及见得后也只恁地,都不去行。又有一般人,却只要苦行,后都不去明。如老子之属,他便只是说不要明,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,此道之所以不明也。」
问:「杨氏以极高明而不道中庸,为贤知之过;道中庸而不极高明,为愚不肖之不及。」曰:「贤者过之与知者过之,自是两般。愚者之不及与不肖者之不及,又自是两般。且先理会此四项,令有着落。又与极高明、道中庸之义全不相关。况道中庸最难,若能道中庸,即非不及也。」
第六章
舜固是聪明睿知,然又能「好问而好察迩言,乐取诸人以为善」,并合将来,所以谓之大知。若只据一己所有,便有穷尽。贺孙同。
问「隐恶而扬善」。曰:「其言之善者播扬之,不善者隐而不宣,则善者愈乐告以善,而不善者亦无所愧而不复言也。若其言不善,我又扬之于人,说他底不是,则其人愧耻,不复敢以言来告矣。此其求善之心广大如此,人安得不尽以其言来告?而吾亦安有不尽闻之言乎?盖舜本自知,能合天下之知为一人之知,而不自用其知,此其知之所以愈大。若愚者既愚矣,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,此其所以愈愚。惟其知也,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;惟其愚也,故自用其愚,而不复求人之知而愈愚也。」
「执其两端」之「执」,如俗语谓把其两头。
「执其两端」,是折转来取中。愚按:定说在后。
两端如厚薄轻重。「执其两端,用其中于民」,非谓只于二者之间取中。当厚而厚,即厚上是中;当薄而薄,即薄上是中。轻重亦然。
两端不专是中间。如轻重,或轻处是中,或重处是中。炎。
两端未是不中。且如赏一人,或谓当重,或谓当轻,于此执此两端,而求其恰好道理而用之。若以两端为不中,则是无商量了,何用更说「执两端」!
问:「『执两端而量度以取中』,当厚则厚,当薄则薄,为中否?」曰:「旧见钦夫亦要恁地说。某谓此句只是将两端来量度取一个恰好处。如此人合与之百钱,若与之二百钱则过,与之五十则少,只是百钱便恰好。若当厚则厚,自有恰好处,上面更过厚则不中。而今这里便说当厚则厚为中,却是躐等之语。」或问:「伊川曰:『执,谓执持使不得行。』如何?某说此『执』字,只是把此两端来量度取中。」曰:「此『执』字只是把来量度。」
问:「注云:『两端是众论不同之极致。』」曰:「两端是两端尽处。如要赏一人,或言万金,或言千金,或言百金,或言十金。自家须从十金审量至万金,酌中看当赏他几金。」赐。
才卿问:「『两端,谓众论不同之极致。』且如众论有十分厚者,有一分薄者,取极厚极薄之二说而中折之,则此为中矣。」曰:「不然,此乃『子莫执中』也,安得谓之中?两端只是个『起止』二字,犹云起这头至那头也。自极厚以至极薄,自极大以至极小,自极重以至极轻,于此厚薄、大小、轻重之中,择其说之是者而用之,是乃所谓中也。若但以极厚极薄为两端,而中折其中间以为中,则其中间如何见得便是中?盖或极厚者说得是,则用极厚之说;极薄之说是,则用极薄之说;厚薄之中者说得是,则用厚薄之中者之说。至于轻重大小,莫不皆然。盖惟其说之是者用之,不是弃其两头不用,而但取两头之中者以用之也。且如人有功当赏,或说合赏万金,或说合赏千金,或有说当赏百金,或又有说合赏十金。万金者,其至厚也;十金,其至薄也。则把其两头自至厚以至至薄,而精权其轻重之中。若合赏万金便赏万金,合赏十金也只得赏十金,合赏千金便赏千金,合赏百金便赏百金。不是弃万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说,而折取其中以赏之也。若但欲去其两头,而只取中间,则或这头重,那头轻,这头偏多,那头偏少,是乃所谓不中矣,安得谓之中!」才卿云:「或问中却说『当众论不同之际,未知其孰为过孰为不及而孰为中也。故必兼总众说,以执其不同之极处而半折之,然后可以见夫上一端之为过,下一端之为不及,而两者之间之为中』。如先生今说,则或问『半折』之说亦当改。」曰:「便是某之说未精,以此见作文字难。意中见得了了,及至笔下依旧不分明。只差些子,便意思都错了。合改云『故必兼总众说,以执其不同之极处而审度之,然后可以识夫中之所在,而上一端之为过,下一端之为不及』云云。如此,语方无病。」或曰:「孔子所谓『我叩其两端』,与此同否?」曰:「然。竭其两端,是自精至粗,自大至小,自上至下,都与他说,无一毫之不尽。舜之『执两端』,是取之于人者,自精至粗,自大至小,总括包尽,无一善之或遗。」一作:「才卿问:『或问以程子执把两端,使民不行为非。而先生所谓「半折之」,上一端为过,下一端为不及,而两者之间为中,悉无以异于程说。』曰:『非是如此。隐恶扬善,恶底固不问了,就众说善者之中,执其不同之极处以量度之。如一人云长八尺,一人云长九尺,又一人云长十尺,皆长也,又皆不同也。不可便以八尺为不及,十尺为过,而以九尺为中也。盖中处或在十尺上,或在八尺上,不可知。必就三者之说子细量度,看那说是。或三者之说皆不是,中自在七尺上,亦未可知。然后有以见夫上一端之为过,下一端之为不及,而三者之间为中也。「半折」之说,诚为有病,合改』云云。」
「舜其大知」,知而不过,兼行说,「仁在其中矣」。回「择乎中庸」,兼知说。「索隐行怪」不能择,不知。「半涂而废」不能执。不仁。「依乎中庸」,择。「不见知而不悔」。执。
问:「舜是生知,如何谓之『择善』?」曰:「圣人也须择,岂是全无所作为!他做得更密。生知、安行者,只是不似他人勉强耳。尧稽于众,舜取诸人,岂是信采行将去?某尝见朋友好论圣贤等级,看来都不消得如此,圣贤依旧是这道理。如千里马也须使四脚行,驽骀也是使四脚行,不成说千里马都不用动脚便到千里!只是他行得较快尔。」又曰:「圣人说话,都只就学知利行上说。」赐。夔孙录云:「问:『「舜大知」章是行底意多,「回择中」章是知底意多?』曰:『是。』又问:『「择」字,舜分上莫使不得否?』曰:『好问好察,执其两端,岂不得择?尝见诸友好论圣贤等级,这都不消得,他依旧是这道理。且如说圣人生知、安行,只是行得较容易,如千里马云,只是他行得较快尔,而今且学他如何动脚。』」
第八章
问:「颜子择中与舜用中如何?」曰:「舜本领大,不大故着力。」
正淳问:「吕氏云:『颜子求见圣人之止。』或问以为文义未安。」人杰录云:「若曰『求得圣人之中道』,如何?」曰:「此语亦无大利害。但横渠错认『未见其止』为圣人极至之地位耳。作『中道』亦得,或只作『极』字亦佳。」
吕氏说颜子云:「随其所至,尽其所得,据而守之,则拳拳服膺而不敢失;勉而进之,则既竭吾才而不敢缓。此所以恍惚前后而不可为像,求见圣人之止,欲罢而不能也。」此处甚缜密,无些渗漏。
第九章
「中庸不可能」章是「贤者过之」之事,但只就其气禀所长处着力做去,而不知择乎中庸也。
问:「『天下国家可均』,此三者莫是智仁勇之事否?」曰:「他虽不曾分,看来也是智仁勇之事,只是不合中庸。若合中庸,便尽得智仁勇。且如颜子瞻前忽后,亦是未到中庸处。」问:「卓立处是中庸否?」曰:「此方是见,到从之处方是行。又如『知命、耳顺』,方是见得尽;『从心所欲』,方是行得尽。」赐。
公晦问:「『天下国家可均也,爵禄可辞也,白刃可蹈也』,谓资质之近于智而力能勉者,皆足以能之。若中庸,则四边都无所倚着,净净洁洁,不容分毫力。」曰:「中庸便是三者之间,非是别有个道理。只于三者做得那恰好处,便是中庸。不然,只可谓之三事。」
徐孟宝问:「中庸如何是不可能?」曰:「只是说中庸之难行也。急些子便是过,慢些子便不及。且如天下国家虽难均,舍得便均得;今按:「舍」字恐误。爵禄虽难辞,舍得便辞得;蹈白刃亦然。只有中庸却便如此不得,所以难也。」徐曰:「如此也无难。只心无一点私,则事事物物上各有个自然道理,便是中庸。以此公心应之,合道理顺人情处便是,恐亦无难。」曰:「若如此时,圣人却不必言致知、格物。格物者,便是要穷尽物理到个是处,此个道理至难。扬子云说得是:『穷之益远,测之益深。』分明是。」徐又曰:「只以至公之心为大本,却将平日学问积累,便是格物。如此不辍,终须自有到处。」曰:「这个如何当得大本!若使如此容易,天下圣贤煞多。只公心不为不善,此只做得个稍稍贤于人之人而已。圣贤事业,大有事在。须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归宿之地,事至物来,应之不错方是。」徐又曰:「『为人君,止于仁;为人臣,止于敬;为人子,止于孝』,至如『止于慈,止于信』。但只言『止』,便是心止宿之地,此又皆是人当为之事,又如何会错?」曰:「此处便是错。要知所以仁,所以敬,所以孝,所以慈,所以信。仁少差,便失于姑息;敬少差,便失于沽激。毫厘之失,谬以千里,如何不是错!」
第十章
忍耐得,便是「南方之强」。
问:「『南方之强,君子居之』,此『君子』字稍稍轻否?」曰:「然。」
问:「『南、北方之强』,是以风土言;『君子、强者居之』,是以气质言;『和而不流』以下,是学问做出来?」曰:「是。」
风俗易变,惟是通衢所在。盖有四方人杂往来于中,自然易得变迁。若僻在一隅,则只见得这一窟风俗如此,最难变。如西北之强劲正如此。时因论「南方之强」而言此。
问:「『宽柔以教,不报无道』,恐是风气资禀所致。以比『北方之强』,是所谓不及乎强者,未得为理义之强,何为『君子居之』?」曰:「虽未是理义之强,然近理也。人能『宽柔以教,不报无道』,亦是个好人,故为君子之事。」又问:「『和而不流』,『中立而不倚』,『国有道,不变未达之所守』,『国无道,至死不变』:此四者勇之事。必如此,乃能择中庸而守之否?」曰:「非也。此乃能择后工夫。大知之人无俟乎守,只是安行;贤者能择能守,无俟乎强勇。至此样资质人,则能择能守后,须用如此自胜,方能彻头彻尾不失。」又问:「以舜聪明睿智,由仁义行,何待『好问,好察迩言,隐恶扬善』,又须执两端而量度以取中?」曰:「此所以为舜之大知也。以舜之聪明睿智如此,似不用着力,乃能下问,至察迩言,又必执两端以用中,非大知而何!盖虽圣人亦合用如此也。」
「和而不流,中立而不倚。」如和,便有流。若是中,便自不倚,何必更说不倚?后思之,中而不硬健,便难独立,解倒了。若中而独立,不有所倚,尤见硬健处!本录云:「柔弱底中立,则必欹倚。若能中立而不倚,方见硬健处。」
中立久而终不倚,所以为强。
「中立而不倚」,凡或勇或辨,或声色货利,执着一边,便是倚着。立到中间,久久而不偏倚,非强者不能。震。
或问「中立而不倚」。曰:「当中而立,自是不倚。然人多有所倚靠,如倚于勇,倚于智,皆是偏倚处。若中道而立,无所偏倚,把捉不住,久后毕竟又靠取一偏处。此所以要强矫工夫,硬在中立无所倚也。」
问「中立而不倚」。曰:「凡人中立而无所依,则必至于倚着,不东则西。惟强壮有力者,乃能中立,不待所依,而自无所倚。如有病底人,气弱不能自持。它若中立,必有一物凭依,乃能不倚;不然,则倾倒而偃仆矣。此正说强处。强之为言,力有以胜人之谓也。」
「强哉矫!」赞叹之辞。古注:「矫,强貌。」
「强哉矫!」矫,强貌,非矫揉之『矫』。词不如此。
问「国有道,不变塞焉;国无道,至死不变」。曰:「国有道,则有达之理,故不变其未达之所守。若国无道,则有不幸而死之理,故不变其平生之所守。不变其未达之所守易,不变其平生之所守难。」
塞,未达。未达时要行其所学,既达了却变其所学!当不变未达之所守可也。
第十一章
问:「汉艺文志引中庸云:『素隐行怪,后世有述焉。』『素隐』作『索隐』,似亦有理,钩索隐僻之义。『素索』二字相近,恐误作『素』,不可知。」曰:「『素隐』,从来解不分晓。作『索隐』读,亦有理。索隐是『知者过之』,行怪是『贤者过之』。」
问:「『索隐』,集注云:『深求隐僻之理。』如汉儒灾异之类,是否?」曰:「汉儒灾异犹自有说得是处。如战国邹衍推五德之事,后汉谶纬之书,便是隐僻。」赐。
「『素隐行怪』不能择,『半涂而废』不能执。『依乎中庸』,能择也;『不见知而不悔』,能执也。」
问:「『遵道而行,半涂而废』,何以为『知及之而仁不能守』?」曰:「只为他知处不曾亲切,故守得不曾安稳,所以半涂而废。若大知之人,一下知了,千了万当。所谓『吾弗能已』者,只是见到了自住不得耳。」又曰:「『依乎中庸,遯世不见知而不悔。』此两句结上文两节意。『依乎中庸』,便是吾弗为之意;『遯世不见知而不悔』,便是『吾弗能已』之意。」
第十二章
费,道之用也;隐,道之体也。用则理之见于日用,无不可见也。体则理之隐于其内,形而上者之事,固有非视听之所及者。
问:「或说形而下者为费,形而上者为隐,如何?」曰:「形而下者甚广,其形而上者实行乎其间,而无物不具,无处不有,故曰费。费,言其用之广也。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视听所及,故曰隐。隐,言其体微妙也。」
「费是形而下者,隐是形而上者。」或曰:「季丈谓,费是事物之所以然。某以为费指物而言,隐指物之理而言。」曰:「这个也硬杀装定说不得,须是意会可矣。以物与理对言之,是如此。只以理言之,是如此,看来费是道之用,隐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见处。」
问:「形而上下与『费而隐』,如何?」曰:「形而上下者,就物上说;『费而隐』者,就道上说。」
「君子之道费而隐。」和亦有费有隐,不当以中为隐,以和为费。「得其名」处,虽是效,亦是费。「君子之道四」,亦是费。
「费而隐」,只费之中理便是隐。费有极意,至意。自夫妇之愚不肖有所能知能行,以至于极处。圣人亦必有一两事不能知不能行,如夫子问官名、学礼之类是也。若曰理有已上难晓者,则是圣人亦只晓得中间一截道理,此不然也。
问:「至极之地,圣人终于不知,终于不能,何也?不知是『过此以往未之或知』之理否?」曰:「至,尽也。论道而至于尽处,若有小小闲慢,亦不必知,不必能,亦可也。」
或问「圣人不知不能」。曰:「至者,非极至之『至』。盖道无不包,若尽论之,圣人岂能纤悉尽知!伊川之说是。」
圣人不能知不能行者,非至妙处圣人不能知不能行。天地间固有不紧要底事,圣人不能尽知。紧要底,则圣人能知之,能行之。若至妙处,圣人不能知,不能行,粗处却能之,非圣人,乃凡人也。故曰:「天地之大也,人犹有所憾。」
「及其至也」,程门诸公都爱说玄妙,游氏便有「七圣皆迷」之说。设如把「至」作精妙说,则下文「语大语小」,便如何分?诸公亲得程子而师之,都差了!
问:「以孔子不得位,为圣人所不能。窃谓禄位名寿,此在天者,圣人如何能必得?」曰:「中庸明说『大德必得其位』。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,如何不是不能?」又问:「『君子之道四,丘未能一。』此是大伦大法所在,何故亦作圣人不能?」先生曰:「道无所不在,无穷无尽,圣人亦做不尽,天地亦做不尽。此是此章紧要意思。侯氏所引孔子之类,乃是且将孔子装影出来,不必一一较量。」
问:「『语小天下莫能破』,是极其小而言之。今以一发之微,尚有可破而为二者。所谓『莫能破』,则足见其小。注中谓『其小无内』,亦是说其至小无去处了。」曰:「然。」
「莫能破」,只是至小无可下手处,破他不得。赐。
问「至大无外,至小无内」。曰:「如云『天下莫能载』,是无外;『天下莫能破』,是无内。谓如物有至小,而尚可破作两边者,是中着得一物在。若云无内,则是至小,更不容破了。」
问:「『其大无外,其小无内』二句,是古语,是自做?」曰:「楚词云:『其小无内,其大无垠。』」
「鸢飞鱼跃」,胡乱提起这两件来说。
问:「鸢有鸢之性,鱼有鱼之性,其飞其跃,天机自完,便是天理流行发见之妙处。故子思姑举此一二,以明道之无所不在否?」曰:「是。」
问「鸢飞鱼跃」之说。曰:「盖是分明见得道体随时发见处。察者,着也,非『察察』之『察』。去伪录作:「非审察之『察』。」诗中之意,本不为此。中庸只是借此两句形容道体。诗云:『遐不作人!』古注并诸家皆作『远』字,甚无道理。记注训『胡』字,最妙。」
鸢飞鱼跃,道体随处发见。谓道体发见者,犹是人见得如此,若鸢鱼初不自知。察,只是着。天地明察,亦是着也。君子之道,造端乎夫妇之细微,及其至也,着乎天地。至,谓量之极
「鸢飞鱼跃」两句。问曰:「莫只是鸢飞鱼跃,无非道体之所在?犹言动容周旋,无非至理;出入语默,无非妙道。『言其上下察也』,此一句只是解上面,如何?」曰:「固是。」又曰:「恰似禅家云『青青绿竹,莫匪真如;粲粲黄花,无非般若』之语。」
皆是费,如鸢飞亦是费,鱼跃亦是费。而所以为费者,试讨个费来看。又曰:「鸢飞可见,鱼跃可见,而所以飞,所以跃,果何物也?中庸言许多费而不言隐者,隐在费之中。」
问「鸢飞鱼跃」集注一段。曰:「鸢飞鱼跃,费也。必有一个甚么物使得它如此,此便是隐。在人则动静语默,无非此理,只从这里收一收,谓心。这个便在。」赐。
问:「『鸢飞鱼跃』如何与它『勿忘、勿助长』之意同?」曰:「孟子言『勿忘、勿助长』本言得粗。程子却说得细,恐只是用其语句耳。如明道之说,却不曾下『勿』字,盖谓都没耳。其曰『正当处』者,谓天理流行处,故谢氏亦以此论曾点事。其所谓『勿忘、勿助长』者,亦非立此在四边做防检,不得犯着。盖谓俱无此,而皆天理之流行耳。钦夫论语中误认其意,遂曰:『不当忘也,不当助长也。』如此,则拘束得曾点更不得自在,却不快活也。」
「活泼泼地。」所谓活者,只是不滞于一隅。
邠老问:「『鸢飞戾天,鱼跃于渊』,诗中与子思之言如何?」曰:「诗中只是兴『周王寿考,遐不作人』!子思之意却是言这道理昭著,无乎不在,上面也是恁地,下面也是恁地。」曰:「程子却于『勿忘、勿助长』处引此,何也?」曰:「此又是见得一个意思活泼泼地。」曰:「程子又谓『会不得时,只是弄精神』,何也?」曰:「言实未会得,而扬眉瞬目,自以为会也。『弄精神』,亦本是禅语。」
子合以书问:「中庸『鸢飞鱼跃』处,明道云:『会得时活泼泼地,不会得只是弄精神。』惟上蔡看破。先生引君臣父子为言此吾儒之所以异于佛者,如何?」曰:「鸢飞鱼跃,只是言其发见耳。释氏亦言发见,但渠言发见,却一切混乱。至吾儒须辨其定分,君臣父子皆定分也。鸢必戾于天,鱼必跃于」
「鸢飞鱼跃」,某云:「其飞其跃,必是气使之然。」曰:「所以飞、所以跃者,理也。气便载得许多理出来。若不就鸢飞鱼跃上看,如何见得此理?」问:「程子云『若说鸢上面更有天在,说鱼下面更有地在』,是如何?」先生默然微诵曰:「『天有四时,春秋冬夏,风雨霜露,无非教也。地载神气,神气风霆,风霆流形,庶物露生,无非教也。』便觉有悚动人处!」炎。
「鸢飞鱼跃。」上文说天地万物处,皆是。「洋洋乎发育万物,峻极于天」也,道体无所不在也。又有无穷意思,又有道理平放在彼意思。上鸢下鱼,见者皆道,应之者便是。明道答横渠书意是「勿忘、勿助长」,即是私意,着分毫之力是也。○「弄精神」,是操切做作也,所以说:「知此,则入尧舜气象。」○「不与天下事」,「对时育物」意思也。○理会「鸢飞鱼跃」,只上蔡语二段、明道语二段看。○上蔡言「与点」意,只是不矜负作为也。五峰说妙处,只是弄精神意思。○「察」字亦作「明」字说。钦夫却只说飞跃意,与上文不贯。
问:「先生旧说程先生论『子思吃紧为人处,与「必有事焉,而勿正心」之意同,活泼泼地』,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两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,初无凝滞倚着之意。今说却是将『必有事焉』作用功处说,如何?」曰:「必是如此,方能见得这道理流行无碍也。」
问「中庸言『费而隐』」。文蔚谓:「中庸散于万事,即所谓费;惟『诚』之一字足以贯之,即所谓隐。」曰:「不是如此,费中有隐,隐中有费。凡事皆然,非是指诚而言。」文蔚曰:「如天道流行,化育万物,其中无非实理。洒埽应对,酬酢万变,莫非诚意寓于其间,是所谓『费而隐』也。」曰:「不然也。鸢飞鱼跃,上下昭著,莫非至理。但人视之不见,听之不闻,分将出来不得,须是于此自有所见。」因谓:「明道言此,引孟子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,勿忘勿助长』为证。谢上蔡又添入夫子『与点』一事。」且谓:「二人之言,各有着落。」文蔚曰:「明道之意,只说天理自然流行;上蔡则形容曾点见道而乐底意思。」先生默然。又曰:「今且要理会『必有事焉』,将自见得。」又曰:「非是有事于此,却见得一个物事在彼。只是『必有事焉』,便是本色。」文蔚曰:「于有事之际,其中有不能自已者,即此便是。」曰:「今且虚放在此,未须强说。如虚着一个红心时,复射一射,久后自中。子思说鸢飞鱼跃,今人一等忘却,乃是不知它那飞与跃;有事而正焉,又是迭教它飞,捉教它跃,皆不可。」又曰:「如今人所言,皆是说费;隐元说不得。所谓『天有四时,春秋冬夏,风雨霜露,无非教也。地载神气,神气风霆,风霆流行,庶物露生,无非教也』。孔子谓『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』,『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』是也。」
问:「『必有事焉』,在孟子论养气,只是谓『集义』也。至程子以之说鸢飞鱼跃之妙,乃是言此心之存耳。」曰:「孟子所谓『必有事焉』者,言养气当用工夫,而所谓工夫,则集义是也,非便以此句为集义之训之。至程子则借以言是心之存,而天理流行之妙自见耳,只此一句已足。然又恐人大以为事得重,则天理反塞而不得行,故又以『勿正心』言之,然此等事易说得近禅去。」广云:「所谓『易说得近禅』者,莫是如程子所谓『事则不无,拟心则差』之说否?」曰:「也是如此。」广云:「若只以此一句说,则易得近禅,若以全章观之,如『费而隐』与『造端乎夫妇』两句,便自与禅不同矣。」曰:「须是事事物物上皆见得此道理,方是。他释氏也说『佛事门中,不遗一法』,然又却只如此说,看他做事,却全不如此。」广云:「旧来说,多以圣人天地之所不知不能及鸢飞鱼跃为道之隐,所以易入于禅。唯谢氏引夫子『与点』之事以明之,实为精切。故程子谓:『「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」,言乐而得其所也。盖孔子之志在于「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」,要使万物各得其性。曾点知之,故孔子喟然叹曰:「吾与点也!」曰:「曾点他于事事物物上真个见得此道理,故随所在而乐。」广云:「若释氏之说,鸢可以跃渊,鱼可以戾天,则反更逆理矣!」曰:「是。他须要把道理来倒说,方是玄妙。」广云:「到此已两月,蒙先生教诲,不一而足。近来静坐时,收敛得心意稍定,读书时亦觉颇有意味。但广老矣,望先生痛加教诲!」先生笑曰:「某亦不敢不尽诚。如今许多道理,也只得恁地说。然所以不如古人者,只欠个古人真见尔。且如曾子说忠恕,是他开眼便见得真个可以一贯。忠为体,恕为用,万事皆可以一贯。如今人须是对册子上安排对副,方始说得近似。少间不说,又都不见了,所以不济事。」正淳云:「某虽不曾理会禅,然看得来,圣人之说皆是实理。故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,夫夫妇妇,皆是实理流行。释氏则所见偏,只管向上去,只是空理流行尔。」曰:「他虽是说空理,然真个见得那空理流行。自家虽是说实理,然却只是说耳,初不曾真个见得那实理流行也。释氏空底,却做得实;自家实底,却做得空,紧要处只争这些子。如今伶利者虽理会得文义,又却不曾真见;质朴者又和文义都理会不得。譬如撑船,着浅者既已着浅了,看如何撑,无缘撑得动。此须是去源头决开,放得那水来,则船无大小,无不浮矣。韩退之说文章,亦说到此,故曰:『气,水也;言,浮物也。水大,则物之小大皆浮。气盛,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。』」广云:「所谓『源头工夫』,莫只是存养修治底工夫否?」曰:「存养与穷理工夫皆要到。然存养中便有穷理工夫,穷理中便有存养工夫。穷理便是穷那存得底,存养便是养那穷得底。」
问:「语录云:『「鸢飞戾天,鱼跃于渊」,此与「必有事焉而勿正心」之意同。』或问中论此云:『程子离人而言,直以此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。上蔡所谓「察见天理,不用私意」,盖小失程子之本意。』据上蔡是言学者用功处。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』之时,平铺放着,无少私意,气象正如此,所谓『鱼川泳而鸟云飞』也,不审是如此否?」曰:「此意固是,但他说『察』字不是也。」
杨氏解「鸢飞鱼跃」处云:「非体物者,孰能识之?」此是见处不透。如上蔡即云:「天下之至显也。」而杨氏反微之矣!
问:「或问中谓:『循其说而体验之,若有以使人神识飞扬,眩瞀迷惑,无所底止。』所谓『其说』者,莫是指杨先生『非体物不遗者,其孰能察之』之说否?」曰:「然。不知前辈读书,如何也恁卤莽?据『体物而不遗』一句,乃是论鬼神之德为万物之体干耳。今乃以为体察之『体』,其可耶?」
问:「『上下察』,是此理流行,上下昭著。下面『察乎天地』,是察见天地之理,或是与上句『察』字同意?」曰:「与上句『察』字同意,言其昭著遍满于天地之间。」
问:「『上下察』与『察乎天地』,两个『察』字同异?」曰:「只一般。此非观察之『察』,乃昭著之意,如『文理密察』,『天地明察』之『察』。经中『察』字,义多如此。」闳祖录云:「『事地察』,『天地明察』,『上下察』,『察乎天地』,『文理密察』,皆明着之意。」
亚夫问:「中庸言『造端乎夫妇』,何也?」曰:「夫妇者,人伦中之至亲且密者。夫人所为,盖有不可告其父兄,而悉以告其妻子者。昔宇文泰遗苏绰书曰:『吾平生所为,盖有妻子所不能知者,公尽知之。』然则男女居室,岂非人之至亲且密者欤?苟于是而不能行道,则面前如有物蔽焉,既不能见,且不能行也。所以孔子有言:『人而不为周南、召南,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!』」
「造端乎夫妇」,言至微至近处;「及其至也」,言极尽其量。
或问:「中庸说道之费隐,如是其大且妙,后面却只归在『造端乎夫妇』上,此中庸之道所以异于佛老之谓道也。」曰:「须更看所谓『优优大哉!礼仪三百,威仪三千』处。圣人之道,弥满充塞,无少空阙处。若于此有一毫之差,便于道体有亏欠也。若佛则只说道无不在,无适而非道;政使于礼仪有差错处,亦不妨,故它于此都理会不得。庄子却理会得,又不肯去做。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说孔子,恰似快刀利剑斫将去,更无些子窒碍,又且句句有着落。如所谓『易以道阴阳,春秋以道名分』,可煞说得好!虽然如此,又却不肯去做。然其才亦尽高,正所谓『知者过之』。」曰:「看得庄子比老子,倒无老子许多机械。」曰:「亦有之。但老子则犹自守个规模子去做,到得庄子出来,将他那窠窟尽底掀番了,故他自以为一家。老子极劳攘,庄子较平易。」
公晦问「君子之道费而隐」,云:「许多章都是说费处,却不说隐处。莫所谓隐者,只在费中否?」曰:「惟是不说,乃所以见得隐在其中。旧人多分画将圣人不知不能处做隐,觉得下面都说不去。且如『鸢飞戾天,鱼跃于渊』,亦何尝隐来?」又问:「此章前说得恁地广大,末梢却说『造端乎夫妇』,乃是指其切实做去,此吾道所以异于禅、佛?」曰:「又须看『经礼三百,威仪三千』。圣人说许多广大处,都收拾做实处来。佛老之学说向高处,便无工夫。圣人说个本体如此,待做处事事着实,如礼乐刑政,文为制度,触处都是。缘他本体充满周足,有些子不是,便亏了它底。佛是说做去便是道,道无不存,无适非道,有一二事错也不妨。」
第十三章
问:「『道不远人,人之为道而远人,不可以为道』,莫是一章之纲目否?」曰:「是如此。所以下面三节,又只是解此三句。」
「人之为道而远人」,如「为仁由己」之「为」;「不可以为道」,如「克己复礼为仁」之「为」。
「君子以人治人,改而止。」未改以前,却是失人道;既改,则便是复得人道了,更何用治它。如水本东流,失其道而西流;从西边遮障得,归来东边便了。
问:「『君子以人治人,改而止。』其人有过,既改之后,或为善不已,或止而不进,皆在其人,非君子之所能预否?」曰:「非然也。能改即是善矣,更何待别求善也?天下只是一个善恶,不善即恶,不恶即善。如何说既能改其恶,更用别讨个善?只改底便是善了。这须看他上文,它紧要处全在『道不远人』一句。言人人有此道,只是人自远其道,非道远人也。人人本自有许多道理,只是不曾依得这道理,却做从不是道理处去。今欲治之,不是别讨个道理治他,只是将他元自有底道理,还以治其人。如人之孝,他本有此孝,它却不曾行得这孝,却乱行从不孝处去。君子治之,非是别讨个孝去治它,只是与他说:『你这个不是。你本有此孝,却如何错行从不孝处去?』其人能改,即是孝矣。不是将他人底道理去治他,又不是分我底道理与他。他本有此道理,我但因其自有者还以治之而已。及我自治其身,亦不是将它人底道理来治我,亦只是将我自思量得底道理,自治我之身而已,所以说『执柯伐柯,其则不远』。『执柯以伐柯』,不用更别去讨法则,只那手中所执者便是则。然『执柯以伐柯,睨而视之,犹以为远』。若此个道理,人人具有,纔要做底便是,初无彼此之别。放去收回,只在这些子,何用别处讨?故中庸一书初间便说『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』。此是如何?只是说人人各具此个道理,无有不足故耳。它从上头说下来,只是此意。」又曰:「『所求乎子,以事父未能也。』每常人责子,必欲其孝于我,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否?以我责子之心,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,此便是则也。『所求乎臣,以事君未能也。』常人责臣,必欲其忠于我,然不知我之事君者尽忠否?以我责臣之心,而反求之于我,则其则在此矣。」又曰:「『所求乎子,以事父未能也。』须要如舜之事父,方尽得子之道。若有一毫不尽,便是道理有所欠阙,便非子之道矣。『所求乎臣,以事君未能也。』须要如舜周公之事君。若有一毫不尽,便非臣之道矣。无不是如此,只缘道理当然,自是住不得。」
问「以众人望人则易从」。曰:「道者,众人之道,众人所能知能行者。今人自做未得众人耳。」此众人,不是说不好底人。
问:「『以众人望人则易从』,此语如何?」曰:「此语似亦未稳。」
蜚卿问:「忠恕即道也,而曰『违道不远』,何耶?」曰:「道是自然底。人能忠恕,则去道不远。」
「施诸己而不愿,亦勿施于人」,此与「己所不欲﹐勿施于人」一般,未是自然,所以「违道不远」,正是学者事。「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,吾亦欲无加诸人」,此是成德事。
「凡人责人处急,责己处缓;爱己则急,爱人则缓。若拽转头来,便自道理流行。」因问:「『施诸己而不愿,亦勿施诸人』,此只是恕,何故子思将作忠恕说?」曰:「忠恕两个离不得。方忠时,未见得恕;及至恕时,忠行乎其间。『施诸己而不愿,亦勿施诸人』,非忠者不能也。故曰:『无忠,做恕不出来。』」
第十四章
「行险侥幸」,本是连上文「不愿乎其外」说。言强生意智,取所不当得。
第十六章
问:「鬼神之德如何?」曰:「自是如此。此言鬼神实然之理,犹言人之德。不可道人自为一物,其德自为德。」
有是实理,而后有是物,鬼神之德所以为物之体而不可遗也。
问:「『体物而不可遗』,是有此物便有鬼神,凡天下万物万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?」曰:「不是有此物时便有此鬼神,说倒了。乃是有这鬼神了,方有此物;及至有此物了,又不能违夫鬼神也。『体物而不可遗』,用拽转看。将鬼神做主,将物做宾,方看得出是鬼神去体那物,鬼神却是主也。」
诚者,实有之理。「体物」,言以物为体。有是物,则有是诚。
鬼神主乎气而言,只是形而下者。但对物而言,则鬼神主乎气,为物之体;物主乎形,待气而生。盖鬼神是气之精英,所谓『诚之不可掩』者。诚,实也。言鬼神是实有者,屈是实屈,伸是实伸。屈伸合散,无非实者,故其发见昭昭不可掩如此。
问:「鬼神,上言二气,下言祭祀,是如何?」曰:「此『体物不可遗』也。『体物』,是与物为体。」炎。
林一之问:「万物皆有鬼神,何故只于祭祀言之?」曰:「以人具是理,故于人言。」又问:「体物何以引『干事』?」曰:「体干是主宰。」按:「体物」是与物为体,「干事」是与事为干,皆倒文。
精气就物而言,魂魄就人而言,鬼神离乎人而言。不曰屈伸往来,阴阳合散,而曰鬼神,则鬼神盖与天地通,所以为万物之体,而物之终始不能遗也。
或问:「鬼神『体物而不可遗』,只是就阴阳上说。末后又却以祭祀言之,是如何?」曰:「此是就其亲切着见者言之也。若不如此说,则人必将风雷山泽做一般鬼神看,将庙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。故即其亲切着见者言之,欲人会之为一也。」
问:「『鬼神之德其盛矣乎!』此止说嘘吸聪明之鬼神。末后却归向『齐明盛服以承祭祀,洋洋乎如在其上』,是如何?」曰:「惟是齐戒祭祀之时,鬼神之理着。若是他人,亦是未晓得,它须道风雷山泽之鬼神是一般鬼神,庙中泥塑底又是一般鬼神,只道有两样鬼神。所以如此说起,又归向亲切明着处去,庶几人知得不是二事也。」汉卿问:「鬼神之德,如何是良能、功用处?」曰:「论来只是阴阳屈伸之气,只谓之阴阳亦可也。然必谓之鬼神者,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。今又须从良能功用上求见鬼神之德,始得。前夜因汉卿说个修养,人死时气冲突,知得焄蒿之意亲切,谓其气袭人,知得凄怆之意分明。汉武李夫人祠云:『其风肃然。』今乡村有众户还赛祭享时,或有肃然如阵风,俗呼为『旋风』者,即此意也。」因及修养,且言:「苌宏死,藏其血于地,三年化为碧,此亦是汉卿所说『虎威』之类。」贺孙云:「应人物之死,其魄降于地,皆如此。但或散或微,不似此等之精悍,所谓『伯有用物精多,则魂魄强』,是也。」曰:「亦是此物禀得魄最盛。又如今医者定魄药多用虎睛,助魂药多用龙骨。魄属金,金西方,主肺与魄。虎是阴属之最强者,故其魄最盛。魂属木,木东方,主肝与魂。龙是阳属之最盛者,故其魂最强。龙能驾云飞腾,便是与气合;虎啸则风生,便是与魄合。虽是物之最强盛,然皆堕于一偏。惟人独得其全,便无这般磊磈。」因言:「古时所传安期生之徒,皆是有之。也是被他炼得气清,皮肤之内,肉骨皆已融化为气,其气又极其轻清,所以有『飞升脱化』之说。然久之渐渐消磨,亦澌尽了。渡江以前,说甚吕洞宾锺离权,如今亦不见了。」因言:「鬼火皆是未散之物,如马血,人战斗而死,被兵之地皆有之。某人夜行淮甸间,忽见明灭之火横过来当路头。其人颇勇,直冲过去,见其皆似人形,髣佛如庙社泥塑未装饰者。亦未散之气,不足畏。『宰我问鬼神』一章最精密,包括得尽,亦是当时弟子记录得好。」
问:「中庸『鬼神』章首尾皆主二气屈伸往来而言,而中间『洋洋如在其上』,乃引『其气发扬于上,为昭明、焄蒿、凄怆』,此乃人物之死气,似与前后意不合,何也?」曰:「死便是屈,感召得来,便是伸。」问:「『昭明、焄蒿、凄怆』,是人之死气,此气会消了?」曰:「是。」问:「伸底只是这既死之气复来伸否?」曰:「这里便难恁地说。这伸底又是别新生了。」问:「如何会别生?」曰:「祖宗气只存在子孙身上,祭祀时只是这气,便自然又伸。自家极其诚敬,肃然如在其上,是甚物?那得不是伸?此便是神之着也。所以古人燎以求诸阳,灌以求诸阴。谢氏谓『祖考精神,便是自家精神』,已说得是。」
问:「『洋洋如在其上,如在其左右』,似亦是感格意思,是自然如此。」曰:「固是。然亦须自家有以感之,始得。上下章自恁地说,忽然中间插入一段鬼神在这里,也是鸢飞鱼跃底意思。所以末梢只说『微之显,诚之不可揜也如此』。」
「微之显,诚之不可揜如此夫!」皆实理也。
问:「鬼神是『功用』、『良能』?」曰:「但以一屈一伸看,一伸去便生许多物事,一屈来更无一物了,便是『良能』、『功用』。」问:「便是阴阳去来?」曰:「固是。」问:「在天地为鬼神,在人为魂魄否?」曰:「死则谓之『魂魄』,生则谓之『精气』,天地公共底谓之『鬼神』,是恁地模样。」又问:「体物而不可遗。」曰:「只是这一个入毫厘丝忽里去,也是这阴阳;包罗天地,也是这阴阳。」问:「是在虚实之间否?」曰:「都是实,无个虚底。有是理,便有是气;有是气,便有是形,无非实者。」又云:「如夏月嘘出固不见,冬月嘘出则可见矣。」问:「何故如此?」曰:「春夏阳,秋冬阴。以阳气散在阳气之中,如以热汤入放热汤里去,都不觉见。秋冬,则这气如以热汤搀放水里去,便可见。」又问:「『使天下之人,齐明盛服以承祭祀』,若有以使之。」曰:「只是这个所谓『昭明、焄蒿、凄怆』者,便只是这昭明是光景,焄蒿是蒸羇,凄怆是有一般感人,使人惨栗,如所谓『其风肃然』者。」问:「此章以太极图言,是所谓『妙合而凝』也。」曰:「『立天之道,曰阴与阳;立地之道,曰柔与刚;立人之道,曰仁与义』,便是『体物而不可遗』。」章句。
或问「鬼神者,造化之迹」。曰:「风雨霜露,四时代谢。」又问:「此是迹,可得而见。又曰『视之不可得见,听之不可得闻』,何也?」曰:「说道无,又有;说道有,又无。物之生成,非鬼神而何?然又去那里见得鬼神?至于『洋洋乎如在其上』,是又有也。『其气发扬于上,为昭明、焄蒿、凄怆』,犹今时恶气中人,使得人恐惧凄怆,此百物之精爽也。」
萧增光问「鬼神造化之迹」。曰:「如日月星辰风雷,皆造化之迹。天地之间,只是此一气耳。来者为神,往者为鬼。譬如一身,生者为神,死者为鬼,皆一气耳。」
「鬼神者,造化之迹。」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见,于其气之往来屈伸者足以见之。微鬼神,则造化无迹矣。横渠「物之始生」一章尤说得分晓。
「鬼神者,二气之良能」,是说往来屈伸乃理之自然,非有安排布置,故曰「良能」也。
「伊川谓『鬼神者,造化之迹』,却不如横渠所谓『二气之良能』。」直卿问:「如何?」曰:「程子之说固好,但在浑沦在这里。张子之说分明,便见有个阴阳在。」曰:「如所谓『功用则谓之鬼神』,也与张子意同。」曰:「只为他浑沦在那里。」闾丘曰:「明则有礼乐,幽则有鬼神。」曰:「只这数句,便要理会。明,便如何说礼乐?幽,便如此说鬼神?须知乐便属神,礼便属鬼。它此语落着,主在鬼神。」直卿曰:「向读中庸所谓『诚之不可揜』处,窃疑谓鬼神为阴阳屈伸,则是形而下者;若中庸之言,则是形而上者矣。」曰:「今且只就形而下者说来,但只是他皆是实理处发见。故未有此气,便有此理;既有此理,必有此」
问:「『鬼神者,造化之迹也。』此莫是造化不可见,唯于其气之屈伸往来而见之,故曰迹?『鬼神者,二气之良能。』此莫是言理之自然,不待安排?」曰:「只是如此。」
「鬼神者,造化之迹。」神者,伸也,以其伸也;鬼者,归也,以其归也。人自方生,而天地之气只管增添在身上,渐渐大,渐渐长成。极至了,便渐渐衰耗,渐渐散。言鬼神,自有迹者而言之;言神,只言其妙而不可测识。
以二气言,则鬼者,阴之灵也;神者,阳之灵也。以一气言,则至而伸者为神,反而归者为鬼。一气即阴阳运行之气,至则皆至,去则皆去之谓也。二气谓阴阳对峙,各有所属。如气之呼吸者有魂,魂即神也,而属乎阳;耳目鼻口之类为魄,魄即鬼也,而属乎阴。「精气为物」,精与气合而生者也;「游魂为变」,则气散而死,其魄降矣。
「『阳魂为神,阴魄为鬼。』『鬼,阴之灵;神,阳之灵。』此以二气言也。然二气之分,实一气之运。故凡气之来而方伸者为神,气之往而既屈者为鬼;阳主伸,阴主屈,此以一气言也。故以二气言,则阴为鬼,阳为神;以一气言,则方伸之气,亦有伸有屈。其方伸者,神之神;其既屈者,神之鬼。既屈之气,亦有屈有伸。其既屈者,鬼之鬼;其来格者,鬼之神。天地人物皆然,不离此气之往来屈伸合散而已,此所谓『可错综言』者也。」因问:「『精气为物』,阴精阳气聚而成物,此总言神;『游魂为变』,魂游魄降,散而成变,此总言鬼,疑亦错综而言?」曰:「然。此所谓『人者,鬼神之会也』。」
问:「性情功效,固是有性情便有功效,有功效便有性情。然所谓性情者,莫便是张子所谓『二气之良能』否?所谓功效者,莫便是程子所谓『天地之功用』否?」曰:「鬼神视之而不见,听之而不闻,人须是于那良能与功用上认取其德。」
「视之而不见,听之而不闻」是性情,「体物而不可遗」是功效。
问:「性情功效,性情乃鬼神之情状;不审所谓功效者何谓?」曰:「能『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』便是功效。」问:「魄守体,有所知否?」曰:「耳目聪明为魄,安得谓无知?」问:「然则人之死也,魂升魄降,是两处有知觉也。」曰:「孔子分明言:『合鬼与神,教之至也。』当祭之时,求诸阳,又求诸阴,正为此,况祭亦有报魄之说。」
问:「『鬼神之为德』,只是言气与理否?」曰:「犹言性情也。」问:「章句说『功效』,如何?」曰:「鬼神会做得这般事。」因言:「鬼神有无,圣人未尝决言之。如言『之死而致死之,不仁;之死而致生之,不知』,『于彼乎?于此乎』之类,与明道语上蔡『恐贤问某寻』之意同。」问:「五庙、七庙递迁之制,恐是世代浸远,精爽消亡,故庙有迁毁。」曰:「虽是如此,然祭者求诸阴,求诸阳,此气依旧在;如嘘吸之,则又来。若不如此,则是『之死而致死之』也。盖其子孙未绝,此气接续亦未绝。」又曰:「天神、地祇、山川之神,有此物在,其气自在此,故不难晓。惟人已死,其事杳茫,所以难说。」
问:「南轩:『鬼神,一言以蔽之曰,「诚」而已。』此语如何?」曰:「诚是实然之理,鬼神亦只是实理。若无这理,则便无鬼神,无万物,都无所该载了。『鬼神之为德』者,诚也。德只是就鬼神言,其情状皆是实理而已。侯氏以德别为一物,便不是。」问:「章句谓『性情功效』,何也?」曰:「此与『情状』字只一般。」曰:「横渠谓『二气之良能』,何谓『良能』?」曰:「屈伸往来,是二气自然能如此。」曰:「伸是神,屈是鬼否?」先生以手圈卓上而直指其中,曰:「这道理圆,只就中分别恁地。气之方来皆属阳,是神;气之反皆属阴,是鬼。日自午以前是神,午以后是鬼。月自初三以后是神,十六以后是鬼。」童伯羽问:「日月对言之,日是神,月是鬼否?」曰:「亦是。草木方发生来是神,雕残衰落是鬼。人自少至壮是神,衰老是鬼。鼻息呼是神,吸是鬼。」淳举程子所谓「天尊地卑,乾坤定矣。鼓之以雷霆,润之以风雨」。曰:「天地造化,皆是鬼神,古人所以祭风伯雨师。」问:「风雷鼓动是神,收敛处是鬼否?」曰:「是。魄属鬼,气属神。如析木烟出,是神;滋润底性是魄。人之语言动作是气,属神;精血是魄,属鬼。发用处皆属阳,是神;气定处皆属阴,是魄。知识处是神,记事处是魄。人初生时气多魄少,后来魄渐盛;到老,魄又少,所以耳聋目昏,精力不强,记事不足。某今觉阳有余而阴不足,事多记不得。小儿无记性,亦是魄不足。好戏不定迭,亦是魄不足。」
侯师圣解中庸「鬼神之为德」,谓「鬼神为形而下者,鬼神之德为形而上者」。且如「中庸之为德」,不成说中庸为形而下者,中庸之德为形而上者!
问:「侯氏中庸曰:『总摄天地,斡旋造化,阖辟乾坤,动役鬼神,日月由之而晦明,万物由之而死生者,诚也。』此语何谓?」曰:「这个亦是实有这理,便如此。若无这理,便都无天地,无万物,无鬼神了。不是实理,如何『微之显,诚之不可揜』?」问:「『鬼神造化之迹』,何谓迹?」曰:「鬼神是天地间造化,只是二气屈伸往来。神是阳,鬼是阴。往者屈,来者伸,便有个迹恁地。」淳因举谢氏「归根」之说。先生曰:「『归根』本老氏语,毕竟无归,这个何曾动?」问:「性只是天地之性。当初亦不是自彼来入此,亦不是自此往归彼,只是因气之聚散,见其如此耳。」曰:「毕竟是无归。如月影映在这盆水里,除了这盆水,这影便无了,岂是这影飞上天去归那月里去!又如这花落,便无了,岂是归去那里,明年复来生这枝上?」问:「人死时,这知觉便散否?」曰:「不是散,是尽了,气尽则知觉亦尽。」问:「世俗所谓物怪神奸之说,则如何断?」曰:「世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说,二分亦有此理。多有是非命死者,或溺死,或杀死,或暴病卒死,是他气未尽,故凭依如此。又有是乍死后气未消尽,是他当初禀得气盛,故如此,然终久亦消了。盖精与气合,便生人物,『游魂为变』,便无了。如人说神仙,古来神仙皆不见,只是说后来神仙。如左传伯有为厉,此鬼今亦不见。」问:「自家道理正,则自不能相干。」曰:「亦须是气能配义,始得。若气不能配义,便馁了。」问:「谢氏谓『祖考精神,便是自家精神』,如何?」曰:「此句已是说得好。祖孙只一气,极其诚敬,自然相感。如这大树,有种子下地,生出又成树,便即是那大树也。」
或问:「『颜子死而不亡』之说,先生既非之矣。然圣人制祭祀之礼,所以事鬼神者,恐不止谓但有此理,须有实事?」曰:「若是见理明者,自能知之。明道所谓:『若以为无,古人因甚如此说?若以为有,又恐贤问某寻。』其说甚当。」
问:「中庸十二章,子思论道之体用,十三章言人之为道不在乎远,当即夫众人之所能知能行,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。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道,当随其所居之分,而取足于其身。」曰:「此两章大纲相似。」曰:「第十五章又言进道当有序,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『费而隐』。盖论君子之道,则即人之所行言之,故但及其费,而隐自存。论鬼神之道,则本人之所不见不闻而言,故先及其隐,而后及于费。」曰:「鬼神之道,便是君子之道,非有二也。」
第十七章
问「因其材而笃焉」。曰:「是因材而加厚些子。」
问「气至而滋息为培,气反而流散曰覆」。曰:「物若扶植,种在土中,自然生气凑泊他。若已倾倒,则生气无所附着,从何处来相接?如人疾病,此自有生气,则药力之气依之而生意滋长。若已危殆,则生气流散,而不复相凑矣。」
问:「舜之大德受命,止是为善得福而已。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倾覆,何也?」贺孙录云:「汉卿问:『栽培倾覆,以气至、气反说。上言德而受福,而以气为言,何也?」曰:「只是一理。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。但物之生时自节节长将去,恰似有物扶持也,及其衰也,则自节节消磨将去,恰似个物推倒它。理自如此。唯我有受福之理,故天既佑之,又申之。董仲舒曰:『为政而宜于民,固当受禄于天。』虽只是迭将来说,然玩味之,觉他说得自有意思。」贺孙录云:「上面虽是迭将来,此数语却转得意思好。」又曰:「嘉乐诗下章又却不说其它,但愿其子孙之多且贤耳。此意甚好,然此亦其理之常。若尧舜之子不肖,则又非常理也。」贺孙录同。
第十八章
问:「舜『德为圣人,尊为天子』,固见得天道人道之极致。至文王『以王季为父,武王为子』,此殆非人力可致,而以为无忧,何也?」曰:「文王自公刘太王积功累仁,至文王适当天运恰好处,此文王所以言无忧。如舜大德,而禄位名寿之必得,亦是天道流行,正得恰好处耳。」又曰:「追王之事,今无可证,姑阙之可也。如三年之丧,诸家说亦有少不同,然亦不必如吕氏说得太密。大概只是说『三年之丧通乎天子』云云,本无别意。」
问:「『身不失天下之显名』与『必得其名』,须有些等级不同?」曰:「游杨是如此说,尹氏又破其说,然看来也是有此意。如尧舜与汤武真个争分数,有等级。只看圣人说『谓韶尽美矣,又尽善也;谓武尽美矣,未尽善也』处,便见。」
问:「『周公成文武之德,追王太王王季』,考之武成金縢礼记大传,武成言:「太王肇基王迹,王季其勤王家,我文考文王。」金縢册「乃告太王王季」。大传言牧野之奠,「追王太王王季历文王昌」。疑武王时已追王。」曰:「武王时恐且是呼唤作王,至周公制礼乐,方行其事,如今奉上册宝之类。然无可证,姑阙之可也。」又问:「『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』,是周公制礼时方行,无疑。」曰:「礼家载祀先王服羇冕,祀先公服鷩冕,鷩冕诸侯之服。盖虽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,然不敢以天子之服临其先公,但鷩冕、旒玉与诸侯不同。天子之旒十二玉,盖虽与诸侯同是七旒,但天子七旒十二玉,诸侯七旒七玉耳。」
问:「古无追王之礼,至周之武王周公,以王业肇于太王王季文王,故追王三王。至于组绀以上,则止祀以天子之礼,所谓『葬以士,祭以大夫』之义也。」曰:「然。周礼,祀先王以羇冕,祀先公以鷩冕,则祀先公依旧止用诸侯之礼,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礼耳。」问:「诸儒之说,以为武王未诛纣,则称文王为『文考』,以明文王在位未尝称王之证。及至诛纣,乃称文考为『文王』。然既曰『文考』,则其谥定矣。若如其言,将称为『文公』耶?」曰:「此等事无证佐,皆不可晓,阙之可也。」
问:「丧祭之礼,至周公然后备。夏商而上,想甚简略。」曰:「然。『亲亲长长』,『贵贵尊贤』。夏商而上,大概只是亲亲长长之意。到得周来则又添得许多贵贵底礼数。如『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,封君之子不臣诸父而臣昆弟』。期之丧,天子诸侯绝,大夫降。然诸侯大夫尊同,则亦不绝不降。姊妹嫁诸侯者,则亦不绝不降。此皆贵贵之义。上世想皆简略,未有许多降杀贵贵底礼数。凡此皆天下之大经,前世所未备。到得周公搜剔出来,立为定制,更不可易。」
「『三年之丧,达于天子』,中庸之意,只是主为父母而言,未必及其它者。所以下句云:『父母之丧,无贵贱一也。』」因言:「大凡礼制欲行于今,须有一个简易底道理。若欲尽拘古礼,则繁碎不便于人,自是不可行,不晓他周公当时之意是如何。孔子尝曰:『如用之,则吾从先进。』想亦是厌其繁。」文蔚问:「伯叔父母,古人皆是期丧。今礼又有所谓『百日制,周期服』。然则期年之内,当服其服。往往今人于此多简略。」曰:「居家则可,居官便不可行。所以当时横渠为见天祺居官,凡祭祀之类,尽令天祺代之,他居家服丧服。当时幸而有一天祺居官,故可为之。万一无天祺,则又当如何?便是动辄窒碍难行。」文蔚曰:「今不居官之人,欲于百日之内,略如居父母之丧,期年之内,则服其服,如何?」曰:「私居亦可行之。」
正淳问:「三年之丧,父母之丧,吕氏却作两般。」曰:「吕氏所以如此说者,盖见左氏载周穆后薨,太子寿卒,谓周『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』。左氏说礼,皆是周末衰乱不经之礼,方子录云:「左氏定礼皆当时鄙野之谈,据不得。」无足取者。君举所以说礼多错者,缘其多本左氏也。」贺孙云:「如陈针子送女,先配后祖一段,更是没分晓,古者那曾有这般礼数?」曰:「便是他记礼皆差。某尝言左氏不是儒者,只是个晓事该博、会做文章之人。若公谷二子却是个不晓事底儒者,故其说道理及礼制处不甚差,下得语恁地郑重。」广录云:「只是说得忒煞郑重滞泥,正如世俗所谓山东学究是也。」贺孙因举公羊所断谓孔父「义形于色」,仇牧「不畏强御」,荀息「不食言」,最是断得好。曰:「然。」贺孙又云:「其间有全乱道处,恐是其徒插入,如何?」曰:「是他那不晓事底见识,便写出来,亦不道是不好。若左氏便巧,便文饰回互了。」或云:「以蔡仲废君为行权,卫辄拒父为尊祖,都不是。」曰:「是他不晓事底见识,只知道有所谓『嫡孙承重』之义,便道孙可以代祖,而不知子不可以不父其父。尝谓学记云『多其讯』,注云:『讯,犹问也。』公谷便是『多其讯』。没紧要处,也便说道某言者何?某事者何?」广录同。方子录略。
问:「中庸解载游氏辨文王不称王之说,正矣。先生却曰:『此事更当考。』是如何?」曰:「说文王不称王,固好,但书中不合有『惟九年大统未集』一句。不知所谓九年,自甚时数起?若谓文王固守臣节不称王,则『三分天下有其二』,亦为不可。又书言『太王肇基王迹』,则到太王时,周家已自强盛矣。今史记于梁惠王三十七年书『襄王元年』,而竹书纪年以为后元年,想得当时文王之事亦类此。故先儒皆以为自虞芮质成之后,为受命之元年。」
第十九章
「旅酬」者,以其家臣或乡吏之属大夫则有乡吏。一人先举觯献宾。宾饮毕,即以觯授于执事者,则以献于其长,递递相承,献及于沃盥者而止焉。沃盥,谓执盥洗之事,至贱者也。故曰:「旅酬下为上,所以逮贱也。」
「旅酬」,是客先劝主人,主人复劝客,客又劝次客,次客又劝第三客,以次传去。如客多,则两头劝起。
问「酬,导饮也」。曰:「仪礼:主人酌宾曰献,宾饮主人,主人又自酌而复饮宾,曰酬。宾受之,奠于席前,至旅而后举。」主人饮二杯,宾只饮一杯。疑后世所谓「倍食于宾」者,此也。
问:「如何是『导饮』?」曰:「主人酌以献宾,宾酬主人曰酢。主人又自饮,而复饮宾曰酬。其主人又自饮者,是导宾使饮也。谚云「主人倍食于宾」,疑即此意。但宾受之,却不饮,奠于席前,至旅时亦不举,又自别举爵,不知如何。」又问:「行旅酬时,祭事已毕否?」曰:「其大节目则已了,亦尚有零碎礼数未竟。」又问:「想必须在饮福受胙之后。」曰:「固是。古人酢宾,便是受胙。『胙』与『酢』『昨』字,古人皆通用。」
汉卿问:「『导饮』是如何?」先生历举仪礼献酬之礼。旅酬礼,下为上交劝。先一人如乡吏之属升觯,或二人举觯献宾。宾不饮,却以献执事。执事一人受之,以献于长,以次献,至于沃盥,所谓「逮贱」者也。旅酬后,乐作,献酬之俎未彻,宾不敢旅酬。酬酒,宾奠不举,至旅酬亦不举。更自有一盏在右,为旅盏也。受胙者,古者「胙」字与「酢」字通。受胙者,犹神之酢己也。周礼中「胙席」,又作昨昔之「昨」。谓初未设,只跪拜,彻后方设席。周礼王享先公亦如之。又举尸饮酢之礼。其特祭,每献酬酢甚详,不知合享如何。周礼旅酬六尸。古者男女皆有尸,女尸不知废于何代。杜佑乃谓古无女尸,女尸乃本夷虏之属,后来圣人革之。贺孙因举仪礼士虞礼云:「男,男尸;女,女尸。是古男女皆有尸也。」先生因举陶侃庙南昌南康。每年祭祀,堂上设神位,两厢设生人位。凡为劝首者,至祭时具公服,设马乘仪状甚盛,至于庙,各就两厢之位。其奉祭者献饮食,一同神位之礼。又某处择一乡长状貌甚魁伟者为之。至诸处祭,皆请与同享。此人遇冬春祭多时节,每日大醉也。厌祭,是不用尸者。古者必有为而不用,如祭殇,阴厌、阳厌,是也。
问「燕毛所以序齿也」。曰:「燕时择一人为上宾,不与众宾齿,余者皆序齿。」
问:「吕氏分『修其祖庙』以下一节作『继志』,『序昭穆』以下一节作『述事』,恐不必如此分?」曰:「看得追王与所制祭祀之礼,两节皆通上下而言。吕氏考订甚详,却似不曾言得此意。」又问:「吕氏又分郊社之礼,作立天下之大本处;宗庙之礼,言正天下之大经处。亦不消分。」曰:「此不若游氏说郊社之礼,所谓『惟圣人为能享帝』;禘尝之义,谓『惟孝子为能享亲』,意思甚周密。」
问:「杨氏曰:『玉币以交神明,祼鬯以求神于幽。』岂以天神无声臭气类之可感,止用玉币表自家之诚意,人鬼有气类之可感,故用芬香之酒耶?」曰:「不然。自是天神高而在上,郁鬯之酒感它不着。盖灌鬯之酒却泻入地下去了,所以只可感人鬼,而不可以交天神也。」
「或问中说庙制处,所谓『高祖』者何也?」曰:「四世祖也。『世』与『太』字,古多互用,如太子为世子,太室为世室之类。」
林安卿问:「中庸二昭二穆以次向南,如何?」曰:「太祖居中,坐北而向南。昭穆以次而出向南。某人之说如此乃是。如疏中谓太祖居中,昭穆左右分去列作一排。若天子七庙,恐太长阔。」又曰:「大率论庙制,刘歆之说颇是。」
孙毓云:「外为都宫。太祖在北,二昭二穆,以次而南,出江都集礼。」向作或问时,未见此书,只以意料。后来始见,乃知学不可以不博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