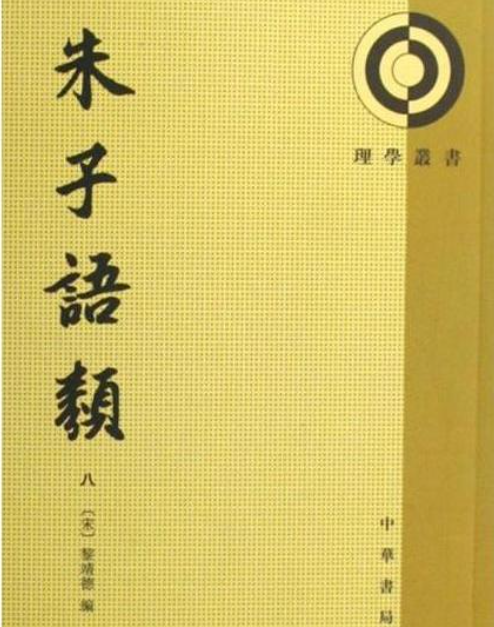本朝六
中兴至今日人物下
宗泽守京城,治兵御戎,以图恢复之计,无所不上表乞回銮,数十表乞不南幸,乞修二圣宫殿,论不割地。其所建论,所谋画,是非利害,昭然可观,观其势骎骎乎中兴之基矣。耿南仲沮之于南京时,势不归京城。汪黄沮之淮甸时,动相掣肘,使不得一有所为。如令桩管器甲之类,不得擅有支遣;问所召募系何色额人,召募得百十万以上人。令京民出助军钱;不得支钱修城池造器械数事,皆汪黄张悫为之。初宗守京,太上即位南京时,河东北、京东西之民,日夜自守,望驾归京。王师之来,全无盗贼。驾一居淮甸,贼起百十万。丁进李成杨进之徒兢起,宗尽召之为用,事垂成而薨。朝廷不为诸人作主,诸人四散为贼矣,伤哉!宗薨时年七十,谥忠简。
宗忠简公薨,其家人方入棺,未敛。军兵轝出大厅,三日祭吊来哭不绝,祭物满厅无数,其得军情人心如此!
王庶西人,赵元镇引作枢密,甚有威望。又言他强倔,死葬庐山。王之奇是庶之子,亦作枢密。庶以私怨杀曲端。端亦西人,庶尝在其军中,几为端所杀。
王子尚初在陕西,为金人所围,求救于曲端。端命一爱将救之,既至,欲求休息数日。王不许,战败,奔入城,王斩之。既而城陷,王奔端。端诘责,欲杀之,有幕僚力谏止,囚之。一日,遣入蜀,遂谮端于魏公,魏公杀端。
徐师川微时,尝游庐山,遇一宦者郑谌,与之诗曰:「平生不善刘蕡策,色色门中看有人。」后入枢府,郑时适用事,模样似有力焉。徐在密院时,金人寇襄阳,中书集议。徐曰:「彼本盗贼所有,时国步未安,盗有窃发据城邑者,因以与之。好时为官,跋扈则为盗。得失不足为国家轻重。」时赵元镇为参知政事,曰:「襄阳为金人所据,则川广路绝,国家危矣!」徐曰:「此是枢密院事,参政不须与。」赵曰:「小小兵事,枢密自主之可也。此国家大事,政府安得不与!」即上马而去。太上闻之,罢徐枢密。徐归乡,以前辈自居,恃文使气好骂,专以饮酒为事,不择贫贱,皆往啖之,诗亦无甚佳者。可学录云:「徐师川在密院,荆襄有密报,五府会议。师川曰:『今日朝廷视荆襄乃无用地,何不弃之?』赵丞相为参政,曰:『此乃上流,何可弃?』师川曰:『密院事,何预参政?』赵曰:『某参知政事,此乃系政事之大者,安得不预!』遂策马径出。入文字,朝廷为之罢师川,赵遂知院,为帅未行,虏退师。」
韩世忠作小官时,一城被围,郡将无计。世忠令募敢死士,得二百人。世忠云:「不消多。」只择得精者八十人,令人持一斧。世忠问云:「其间岂无能为盗者?」遂令往偷了鼓搥,却略将石头去惊他门。他必往报中军,便随入,见有红帐者便斫。俟彼人集,便出来,恐有马军来赶,便与相杀。城上皆喊云:「马军进!」如是果退围。
岳太尉飞本是韩魏公家佃客,每见韩家子弟必拜。
岳飞恃才不自晦。郭子仪晚节保身甚阘冗,然当紧要处,又不然,单骑见虏云云。飞作副枢,便直是要去做。张韩知其谋,便只依违。然便不做亦不免,其用心如此,直是忠勇也!
绍兴间诸将横。刘光世使一将官来奏事,应对之类皆善。上喜之,转官,颇赐予。刘疑其以军中机密上闻,欲杀之。其人走投朝廷,朝廷不知如何区处之。刘又使人逐路杀之,追者已近,其人告州将藏之狱中,入文字朝廷,方免。
吴玠到饶风关却走回,此事惟张巨山退虏记得实。
后世用兵,只是胡冢杀,那曾有节制!如季通说八阵可用,怕也未必可用。当临阵时,只看当时事体排扒得着所在。如吴璘败虏于杀金平,前面对陈交兵正急,后面诸军一齐拥前,烂杀虏人,这有甚陈法?且如用兵前陈交接,后陈即用木车隔了,不令突出。当吴璘那时,军势勇猛,将来隔了,一齐都斫开突前去,有甚陈法?看来兵之胜负,全在勇怯。又云:「用兵之要,敌势急,则自家当委曲以缠绕之;敌势缓,则自家当劲直以冲突之。」
古之战也,两军相对,甚有礼。有馈惠焉,有饮酌焉,不似后世便只是烂杀将去。刘锜顺昌之捷,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后生。当时虏骑大拥而至,凡十余万。诸将会议,以为固知力不能当,然急渡江,则朝廷兵守已自戒严,必不可渡。兼携持老幼,虏骑已迫,必为所追,其势终归于死。若两下皆死,不若固守,庶几可生,遂闭城门而守。虏人大至,刘锜先遣人约他某日战。虏人谓其敢与我约战,大怒。至日,虏骑压于城外。时正暑月,刘锜分部下兵五千为五队,先备暑药,饭食酒肉存在。先以一副兜牟与甲,置之日下晒,时令人以手摸,看热得几何。如此数次,其兜牟与甲尚可容手,则未发。直待热如火,不可容手,乃唤一队军至,令吃酒饭。少定,与暑药,遂各授兵出西门战。少顷,又唤一队上,授之,出南门。如此数队,分诸门迭出迭入,虏遂大败。缘虏人众多,其立无缝,仅能操戈,更转动不得。而我兵执斧直入人丛,掀其马甲,以断其足。一骑纔倒,即压数骑,杀死甚众。况当众正热,甲盾如火,流汗喘息烦闷。而吾军迭出,饱锐清叙,而伤困者,即扶归就药调护。遂以至寡敌至众,虏人大败,方有怯中国之意,遂从和议,前此皆未肯真个要和。此是庚申年六月,可惜此机不遂进!
张栋字彦辅。谓刘信叔亲与他言,顺昌之战,时金人十上万人围了城,城中兵甚不多。刘使人下书约战日,虏人笑。是日早,虏骑迫城下而阵,连山阵甚密不动。刘先以甲一联晒庭中,一边以肉饭犒师。时使人摸甲未大热,又且候。候甲热甚,遂开城门,以所犒一队持斧出,令只掀起虏骑,斫断马脚。人马都全装,一骑倒,又粘倒数骑,虏人全无下手处。此队归,以五苓大顺散与服之,令歇。又以所犒第二队出如前,杀甚多,虏觉得势败,遂遁走。后人问晒甲之事如何,曰:「甲热则虏人在日中皆热闷矣,此则在叙处歇方出。」时当暑月也。
籍溪尝云,建炎间,勤王之师,所过州县,如入无人之境,恣行擒掠,公私苦之。有陈无玷者,以才略称。尝作某县,宿戒邑人,各备器械,候闻锺声,则人执以出,随其所居,相比排列。未几,勤王之师入县,将肆纵横之状,即命击锺。邑人闻之,如其宿戒以出,师徒见其戈矛森列,不虞其有备若此也,相顾失色,遂整师以过,秋毫无犯,邑人德之。又,胡文定公之趋召命也,泛舟而下,无玷走吏致书,戒其吏云:「计程到江黄间,有官舡自下而上者,可扣之,当是本官。」吏至彼,果有舟上者,一问得之,其善料事如此。盖渠以事占之,知文定之不果造朝也。儒用。
某人作县,临行请教于某人。先生言,其姓名今忘记。某人曰:「张直柔在彼,每事可询访之。」某人到官,忽有旨,令诸县造战舡。召匠计之,所费甚巨。因意临行请教之语,亟访策于张。张曰:「此事甚易,可作一小者,计其丈尺广狭长短,即是推之,则大者可见矣。」遂如其语为之,比成推算,比前所计之费减十之三四。其后诸县皆重有科敛,独是邑不扰而辨。后其人知绍兴府,太后山陵,被旨令应副钱数万给砖为墙。其大小厚薄,呼砖匠于后圃依样造之。会其直,比抛降之数减数倍。遂申朝廷,乞绍兴自认砖墙。正中宦者欺弊,遂急沮其请,只令绍兴府应副钱,不得干预砖墙事。儒用。成录云:「其人曰:『如何费许多钱!』遂呼砖匠于园后结墙一堵,验之。先问其砖之大小厚薄,依样烧砖而结之,费比朝廷所抛降之数减数倍云云。」
张觷字直柔。福建人,尝知处州。有人欲造大舟,不能计其所费,问之。张云:「可造一小舟,以寸折尺,便可计算。」后又有人欲筑绍兴围神庙墙,召匠计之,云费八万缗。其人用张法,自筑一丈长,算其墙可直二万,遂以四万与匠者。董事内官无所得,遂与奏绍兴贫,不如自出钱。太后遂自出钱,费三十二万缗。
高宗朝有朝士,后为尚书,建炎尝请驾幸福建,以为福建有天险。又上言,邵武南剑人,多凿纸钱,费农业,乞降旨禁之。或人家忌日之类,不得烧纸钱,只烧经幡一二纸,好笑如此!粘罕长枪大剑如此,而使若辈人谋国云云。邵武有文集。又有赵霈者,清献之孙,此时亦上言,圣节杀鸡鹅太多,只令杀猪羊大牲。适传有一「龙虎大王」南侵,边方以为惧。胡侍郎云:「不足虑,此有『鸡鹅御史』,足以当之!」
绍兴间,曾天隐名恬。作中书舍人。曾亦贤者,然尝为蔡京引用。后修哲宗实录成,太上赵丞相要就褒赏修实录官,制辞上说破前后是非。曾以蔡之故,常主那一边。及行词,只模糊作一修史转官制。上与丞相不乐,命吕居仁行。吕权中书舍人,自丁巳三月二十五日上一状论分别邪正。谓曾之徒,也自荆公诸人熙丰间用事,新经字说之类,已坏了人心术。元佑诸公所为,那一边人终不以为是。绍圣以后,又复新政,败坏一向,至于渡江。然旧人亦多在者,其所见旧染不省,虽贤者亦复如是,如曾之徒是也。因论人以先入为主,一生做病。
汤思退事秦桧最久,其无状皆亲学得,故所为如此之乖。
汤思退作枢密,董德元参政,商量荐小秦作相。董言之不答,汤即背其说,逐董出,召魏良臣来作参。魏治杨存中,上不答。汤又逐出魏,汤遂作相。
汤思退王之望尹穑三人奸甚,又各有文。以计去了魏公,尽毁其边备山寨、水柜之类,凡险要处有备御者,皆毁之。还了金人四州,以谓可以保其和好而无事矣。一日,只见虏骑十万突至,惊扰一番而去。三人者乃罢,其谋盖三人之所同也。尹乃疏平日边事,尹能文其事,尚如此奸。宰相自为一室藏文书,全不令台谏至,其后及贾谊待大臣盘剑之类事。汤卒以惊死败,小人情状如此。初去了魏公,毁边备时,诸将皆欲得而杀之。王之望尚在其所,急上书论三事:一恢复,二守御,三与之和时,亦要地界、岁币之类分明。上大喜,即日召归参大政。乃金人有所须,上商量之际,上意欲不与,欲之望有所说,之望全不言。上顾之云:「如何?」之望曰:「不如且与之。」上曰:「卿前书意如何?」及败,二人皆惧边将之怨己不敢出师,上前至以鄙语相骂。之望谓汤小数子,成把价撒出来,好士夫所为如此之类,言语记不全。三人之意,惟恐奉虏不至,但看要如何。虏见其着数低,易之,遂无所不敢。使其和议如秦桧时,则亦一桧矣。好枭三人首于都市,俾虏人闻之,亦以少畏。此是甲申年。虏骑来时,思退之望既罢,穑不罢。上令胡铨穑往经略边备,二人皆搬家先去。上但知胡如此,怒去之。时召陈鲁公,鲁公至,留胡。上曰:「用其经略边事,遂搬家先去,用是罢之。」陈曰:「如此,则穑亦搬家去。臣途中见之。」遂罢。穑多读书,能文,然行不成人。上初极重之,每对群臣言,无人及穑。龚茂良为左司谏,与穑同对,欲促上早定和议。穑曰:「内政只消三二个月打迭,不日可以至太平。但外敌未去,下手未得,且与讲和为便。」
方伯谟问:「某人如何。」忘其姓名。先生曰:「对移县丞一节,全处不下。」又问:「是当初未见得?」曰:「他当初感发踊跃,只是后来不接续。」语朱希真曰:「天下有一等人,直是要文采,求进用。」因说及尹穑,「前日赵蕃称他是好人。」伯谟问:「他当初如何会许多年不出?」曰:「只是且碍过,及至上手则乱。渠初擢用,力言但得虏和,三二月纲纪自定。龚实之云:『便是他人耳聋,敢如此说!』如减冗官事是,但非其人,行之失人心。渠初除浙西制置,胡邦衡除浙东。邦衡搬家从苏秀,迤欲归乡,因此罢。陈鲁公再用,因言于上曰:『胡铨搬家固可罪,尚向北;尹穑搬家乃向南。』上云:『无此事』。公云:『臣亲见之。自古人主无与天下立敌之理。天下皆道不好,陛下乃力主张。』张魏公在督府,渠欲摇撼。一日,陈彦广对言:『张某似有罢意』。上曰:『安有此事!方今谁出魏公上?(上每呼张相,只曰『魏公』。)必是台谏中为此,卿可宣谕。』陈见尹,道上意,尹云:『某请对。』数日,驾在德寿,批出,陈知建宁府,魏公亦罢。」某问:「当时诸公荐之,何故?」曰:「亦能文章,大抵以此取人,不考义理,无以知其人,多为所误。如苏子由用杨畏,畏为攻向上三人,苏终不迁。畏曰:『苏公不足与矣。』乃反攻之。」
或问胡邦衡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。先生曰:「天生天杀,道之理也,人如何解死得人!」
胡邦衡尚号为有知识者,一日以书与范伯达云:「某解得易,魏公为作序;解得春秋,郑亿年为作序。」以为美事。范答书云:「易得魏公序甚好。郑序春秋者,不知是何人,得非刘豫左相乎?是此人时,且请去之。」胡旧尝见李弥逊,字似之,亦一好前辈。谓胡曰:「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称,只做得一两节好便好。胡后来丧名失节,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。
吕居仁学术虽未纯粹,然切切以礼义廉耻为事,所以亦有助于风俗。今则全无此意。
吕家之学,大率在于儒禅之间,习典故。居仁遂去学作诗,亦不说于赵丞相,后于秦桧所为,亦有辅之者。籍溪云:「尝代一表云:『仰日月于九天之上』,下一句甚卑,可怜之词,居仁为之也。后虏中此文亦有人传之。」
吕居仁作舍人时,缴奏文字好处多。一章论袁焕章乞作教官。「教官人之师表,岂可乞?」此论不闻数十年矣。今皆是陈乞,然不陈乞,朝廷又不为检举。朝廷为检举方是,亦可以养士大夫廉耻。今皆不然,都要陈乞。旧除从官,便不磨勘,今亦不然。如磨勘,大约用三载考绩之法,一年一切了。今年年日日理会官员磨勘。
吕居仁不甚恶赃污,深恶多才刻薄者。此自回避党人,故有此论出来。然大害名教,岂不使得子孙取受!如论固穷守节处,甚佳。
「吕舍人好言忍耻之类,此意不佳。」扬因及刘道原不受温公惠。曰:「如此做得人,也灵利。」
说吕居仁解大学,曰:「他诸公何故一做下便不改动一字?非圣人安能如此?这般非是大圣,便是大愚!」
因说吕居仁作汪民表墓志不好,曰:「作龟山底尤不好,故文定全不用,尽做过了。」
「吕居仁家往往自抬举,他人家便是圣贤。其家法固好,然专恃此,以为道理只如此,却不是。如某人纔见长上,便须尊敬以求教;见年齿纔小,便要教他;多是如此。」人杰因曰:「此乃取其家法而欲施之于他人也。」
汪圣锡不直潘子贱直前事,云:「无缘听得殿上语。」向宜卿云:「吾当时之言,尹和靖某事,又为朱子发理会恤典。子贱当时为吕居仁所卖。」
张无垢说得一般道理,一切险而动。
张无垢气魄,汪端明全无些子气魄。无垢论语说得甚敷畅,横说竖说,居之不疑。
「永嘉前辈觉得却到好,到是近日诸人无意思。陈少南,某向虽不识之,看他举动煞好,虽是有些疏,却无而今许多纤曲。」贺孙问:「少南虽是疏,到在讲筵议论,实有正直气象。」曰:「然。近日许多人,往往到自议论他。」
问:「陈少南诗如何?」曰:「亦间有好处,然疏,又为之甚轻易。秦桧居温州时,陈尝为馆客。后入经筵,因讲公羊『母以子贵』之说为非是,因论嫡妾之分。是时太母还朝,陈遂忤太上意,安置惠州。张宋卿于彼从之。徽庙梓宫归,郑后梓宫亦归,邢后太上初聘,亦随归。及边,以讣闻。太母还,秦桧欲以吉服迎,吴才老时为礼官,独以为不可,谓须先以凶服迎梓宫归。太上几年不见太母了,不争些二三日。奉安梓宫了,却以吉服迎太母归。众礼官聚都堂,皆从秦意,吴独争之。秦曰:『此不是公聚讼处。』即以吴出之。」先生又云:「公羊之说非是,只有一嫡。」
因论李德远黄世永为汤进之所买,云:「他亦是不曾见前辈,前辈皆不如此。汤见人时,一面颜色言语皆买人之物。史直翁亦然,然却较好。史虽主和,然亦有去交结得一人为应者,然许他皆过分数了。诚使彼足以抗虏,此中亦何以处之?其策甚非也。」
史丞相好荐人,极不易;然却有些笼络人意思,不佳。陈丞相较浑厚,无这般意思,又若贤否不辨者。
陈福公自在,只如一无所能底村秀才。梁丞相亦然。
史老虽如此,然尝爱论荐引拔士人,此一节可喜。如陈应求方寸平正,远过龚实之。然龚又却好事,每到处便收拾得些人才。刘枢不好士人,先亦读书,长编从头批抹近得书云,尚要诸经史从头为看一遍,顾老病,恐不能。
因论张戒定夫,其初名节好。后来亦以书与诸公论,当时某不是全不主和议,但谓和时要如何。后来多有如某之料,其意欲进甚锐。太上终是嫌破和议底人。秦桧死,亟下诏守和议不变,用沈该万俟¤陈诚之辈。故张戒自秦桧死后,数年终不用。而张自躁如此,盖是学无本原故耳。张学老子之类。
张定夫居建昌,享高寿,有文集曰正平集。自言初学孔子之道而无所得,后读老子而愿学焉。又喜管子,其议多尚法制。立朝亦可观,人杰录:「与先吏部厚善。当时朝士皆敬之,虽有素喜陵人者,亦不敢慢。」尝对高宗云:「陛下有仁宗之俭慈,而乏艺祖之英略。」高宗以为说得好。又尝言:「过江以来,非李伯纪赵元镇张魏公三人,也立不住。」
先生谓若海曰:「令祖全节翁孝义笃至,又能坚正自守。当时权贵欲一见之,竟不为屈。至于通判公,又为张赵所知,持论凛然,不肯阿附秦老,可谓『无忝于所生』者。前辈高风,诚可敬仰。为子孙者,其忍不思所以奉承而世守之乎!」或曰:「今人志在趋利,闻人道及此等事,则多非讦讪笑。」先生曰:「某尝谓得他当面言之,犹似可。又有口以为是,心实非之,存在胸中,不知不觉做出怪事者,兹尤可畏!」按:胡泳云,内翰,文公之后。
「邓名世吏,临川人,学甚博,赵丞相以白衣起为著作郎。与先吏部同局,吏部甚敬畏之。有考证文字甚多,考证姓氏一部甚详,绍兴府有印板。谓左丘姓,人有牌牓在卖卦,左氏只是姓左。」先生云:「楚左史倚相世为史官,恐其后也。」邓著作后为秦桧以传出秘书文字罪之,褫官勒停。
熊叔雅名彦诗,王时雍婿也。金人入寇,京城不守,时雍尽搜取妇女于虏人,人号时雍为『虏人外公』。当秦桧时,叔雅知永州,魏公时安置永州。秦桧之父曾为玉山知县,玉山人要为老秦立祠堂,求叔雅作记。叔雅质之魏公,魏公令勿须作。叔雅自后只是言贫,这后恐不得差遣。十数日后,魏公知其意,与之曰:「前日所谓祠堂记,作也不妨。」叔雅作之,大意言:人问公有甚异政?曰无异政,只见民父子有亲,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皆如此好了。子太师得其道以治天下亦然,云云。立大碑于玉山。
三山黄明陟登,是黄传正之父。扬录云:「张登福建人。」[莹田-玉]录云:「张致中父登。」从周录云:「永福姓张人。」其人朴实公介,为甚处宰。诸录云尤溪。初上任,凡邑人来见者,都请,诸录云:「士夫僧道百余人。」但一揖。扬录云:「坐处亦不足,只立说话。」问:「诸公能打对否?」人皆不敢对。因云:「『天』对甚?」其中有人云:「对『地』。」又问:「『日』对甚?」云「对『月』。」「『阳』对甚?」云:「对『阴』。」却又问:「『利』对甚?」云:「对『害』。」乃大声云:「这便不是了!天下一切人,都被这些子坏了。才把『害』对『利』,便事事上只见得利害,更不问义理。[莹田-玉]录云:「人只知以『利』对『害』,便只管寻利去。」须知道『利』乃对『义』,才明得义、利,便自无乖争之事。自后只要如此分别,不要更到讼庭。」后来在任果有政声。此事须近于迂阔,然却甚好,今不可多见矣![莹田-玉]录云:「一揖而退,此亦可书。其桃符云:『奉劝邑人依本分,莫将闲事到公庭。』言虽质,意亦好。」扬录云:「其人为政简易,无系累。后坐化死。」
李椿年行经界,先从他家田上量起,今之辅弼能有此心否?
王龟龄学也粗疏。只是他天资高,意思诚悫,表里如一,所至州郡上下皆风动。而今难得此等人!
王詹事守泉。初到任,会七邑宰,劝酒,历告之以爱民之意。出一绝云:「九重天子爱民深,令尹宜怀恻怛心。今日黄堂一杯酒,使君端为庶民斟!」七邑宰皆为之感动。其为政甚严,而能以至诚感动人心,故吏民无不畏爱。去之日,父老儿童攀辕者不计其数,公亦为之垂泪。至今泉人犹怀之如父母!
汪端明学亦平正,然疏。文亦平正,不好小蹊曲径。福建政事镇静,与福亦相宜。蜀政不及。见事亦快。
汪端明少从学于焦先生。汪既达时,从杲老问禅。怜焦之老,欲进之以禅,因劝焦登径山见杲。杲举「寂然不动,感而遂通」。焦曰:「和尚不可破句读书。」不契而归,亦奇士也。焦名援,字公路,南京人,清修苦节之士。
汪圣锡日以亲师取友多识前言往行为事,故其晚年德成行尊,为世名卿。
汪季路甚子细,但为人性太宽,理会事不能得了。
祝怀汝昭尝论张说。一日,祝有一婢溺死。衢守施元之谓张曰:「祝婢乃其父婢,祝污之,恐事泄,抑令其死。」张遂言之于上。上曰:「此事大,若有之,行遣不得草草;若无,不须以此陷人。」遂阴遣一兵士之类来衢探其事。往来月余日,得其实矣。一日,乃投都监曰:「奉圣旨,来探祝编修家公事。」遂叫集邻里作保明状去,事方已。兵士小人,乃能如此。
主上一日嘉郑自明直言,遂问近臣曰:「昔时有一魏掞之好直言,今何在?」左右以死对。问:「有子弟否?」无人为敷陈,遂赠直秘阁宣教郎。
这道理易晦而难明。某少年过莆田,见林谦之方次荣说一种道理,说得精神,极好听,为之踊跃鼓动!退而思之,忘寝与食者数时。好之,念念而不忘。及至后来再过,则二公已死,更无一人能继其学者,也无一个会说了!
论林艾轩作文解经,曰:「林成季井伯为艾轩作墓铭,讳艾轩著书。但云幸学,讲中庸九经及某篇,是艾轩所著。此是有形讳不得底。尝见九经口义,先说一段冒子,全与所讲不干涉。其说是言『巍巍乎惟天为大,唯尧则之』。『巍巍乎,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』!人看时,都理会不得。某却曾见他口说来,乃是说道,巍巍乎者,世上有恁地大底事,惟天有之,惟尧则之。下面又说个『巍巍乎』者,言此大事,只是天与尧有之,舜禹都不与此。盖是取奉光尧,不知却推倒舜禹。」又云:「在兴化南寺,见艾轩言曾点言志一段,『归』,自释音作『馈』字,此是物各付物之意。某云:『如何见得?』艾轩云:『曾点不是要与冠者童子真个去浴沂风雩。只是见那人有冠者,有童子,也有在那里澡浴底,也有在那里乘叙底,也有在那里馈饷馌南亩底。曾点见得这意思,此谓物各付物。』」艾轩甚秘其说,密言于先生也。德辅。
王说习之性直,好人,与林艾轩辈行。上即位即召见,论不可讲和。上一日谓宰臣曰:「前日上殿,有个生得貌寝,是言此。忘了甚底官人,议论亦好。」遂除官。龚实之笑王习之以不讲和奉上意。先生谓习之直,不是奉上。龚实之多读书,知前辈大体,颇识义理。又有才,做得去。亦有文。小官时甚好。为正言时,攻曾龙。后来心术一偏至于如此,可惜!可惜!反不如陈应求,全不如他却较好。
因给舍缴驳事,而大臣无所可否,云:「昔梁叔子将为执政时,曾语刘枢云:『某若当地头,有文字从中出,不当如何,如何也须说教住了,始得。』后梁已大用,而文字自中出者,初不闻有甚执奏。刘枢深怪其事。后见钱某因事说及,丞相煞有力。中出文字,日日有之,丞相每每袖回了而后已。自今观之,又不见此。」
「某人初登宰辅,奏逐姜特立。忽有旨召姜,乞出甚力,在六和塔待命。有旨免宣押。某人初过枢。天下属望,首有召姜之命,经由枢密,曾无奏止,坐视丞相以近习故去国。其意只以入枢未久,恐说不行而去,为人所笑,故放过此一着,是甚小事。」直卿云:「人日日常将理义夹持个身心,庶几遇事住不得。若是平常底人,也是难得不变。如其人,固谓世人属望,但此事亦须不要官爵,方做得。」曰:「固是。若是不要官爵,这一项事如何放得过?每看史策到这般地头,为之汗栗!一个身己便顿在兵刃之间。然汉唐时争议而死,愈死愈争,其争愈力。本朝用刑至宽,而人多畏懦,到合说处,反畏似虎。」至道因问:「武后事,狄梁公虽复正中宗,然大义终不明,做得似鹘突。」曰:「当此时世,只做得到恁地。狄梁公终死于周,然荐得张柬之,迄能反正。」又问:「吕后事势倒做得只如此,然武后却可畏。」曰:「吕后只是一个村妇人,因戚姬,遂迤逦做到后来许多不好。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,合下便有无君之心。自为昭仪,便鸩杀其子,以倾王后。中宗无罪而废之,则武后之罪已定。只可便以此废之,拘于子无废母之义,不得。吕后与高祖同起行伍,识兵略,故布置诸吕与诸军。平勃之成功也,适直吕后病困,故做得许多脚手,平勃亦幸而成功。胡文定谓武后之罪,当告于宗庙社稷而诛之。」又云:「中宗决不敢为黜母之事。然而并中宗废之,又不得。当时人心惟是见武后以非罪废天子,故疾之深;惟是见中宗以无罪被废,故愿复之切。若并中宗废之,又未知有何收拾人心,这般处极难。」
耿京起义兵,为天平军节度使。有张安国者,亦起兵,与京为两军。辛幼安时在京幕下为记室,方衔命来此,致归朝之义,则京已为安国所杀。幼安后归,挟安国马上,还朝以正典刑。儒用。
辛幼安亦是个人才,岂有使不得之理!但明赏罚,则彼自服矣。今日所以用之者,彼之所短,更不问之;视其过当为害者,皆不之恤。及至废置,又不敢收拾而用之。
问:「陈亮可用否?」曰:「朝廷赏罚明,此等人皆可用。如辛幼安亦是一帅材,但方其纵恣时,更无一人敢道它,略不警策之。及至如今一坐坐了,又更不问着,便如终废。此人作帅,亦有胜它人处,但当明赏罚以用之耳。」
近世如汪端明,专理会民;如辛幼安,却是专理会兵,不管民。他这理会兵,时下便要驱以塞海,其势可畏!植。
辛幼安为闽宪,问政,答曰:「临民以宽,待士以礼,驭士以严。」恭甫再为潭帅,律己愈谨,御吏愈严。某谓如此方是。
刘枢帅建康,所得月千。刘欲止受正所当得者,以恐坏后来例,不敢。但受之,后却送其不当得者于公使库。后韩元龙来作漕,尽不受其所不当得者,刘甚称服之。平父云。
刘恭父创第,规模宏丽,先生劝止之曰:「匈奴未灭,何以家为!」忠肃意不乐也。
刘宝学初娶熊氏,生枢密。生次子,方落地,问是男,即命与其弟直阁为子。熊不乐,都不问,竟以是而没。后枢密娶吕氏入门,未几,即命吕一切仪物尽与直阁女为嫁具,吕即送与之。平父云。
金安节为人好。
戴肖望云:「洪景卢杨廷秀争配享,俱出,可谓无党。」曰:「不然。要无党,须是分别得君子小人分明。某尝谓,凡事都分做两边,是底放一边,非底放一边;是底是天理,非底是人欲;是即守而勿失,非即去而勿留,此治一身之法也。治一家,则分别一家之是非;治一邑,则分别一邑之邪正;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,莫不皆然,此直上直下之道。若其不分黑白,不辨是非,而猥曰『无党』,是大乱之道。」戴曰:「信而后谏,意欲委曲以济事。」曰:「是枉尺直寻而可为也!」
孙逢吉从之煞好。初除,便上一文字,尽将今所讳忌如「正心诚意」许多说话,一齐尽说出,看来这是合着说底话。只如今人那个口道是是!那个不多方去回避!
天下事须论一个是不是后,却又论其中节与不中余右失于许,然使其言见听,不无所补。李琪则所谓「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」,要知却亦有以救其失也。如二子,却所谓「是中之不中节」者,
「耿直之作浙漕时,有一榜在客位甚好,说用考课之法。应州县官不许用援,有绩可考,自发荐章。如考课在上而挟贵援者,即降次等。今在镇江亦然否?」曰:「僻在山林,不知其详,但闻私谒不行。」曰:「向来耿守有一书说『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』。」从周曰:「此义当如何说?」曰:「也只是前来说。若如耿说,却是圣人学得些骨董,要把来使,全不自心中流出。」从周曰:「『伊尹耕于有莘之野,而乐尧舜之道。』濂溪曰:『志伊尹之所志,学颜子之所学。』伊尹耻其君,至若挞于市。学者若横此心在胸中,却是志于行,莫不可?」曰:「非是私。修身养性与致君泽民只是一理。」」
吴公路作南剑天柱滩记曰:「事无大小,为之必成;害无大小,除之必去。」此见其志。
王宣子说:「甘抃言,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,以此而出,人皆高之。宦官以承顺为事,忽犯颜而出,谁将你当事!而黄彦节是也。其见如此之乖!后汉吕强,后世无不贤之。」
近年有洪邦直为宰,以赃被讼,求救于伯圭。伯圭荐之甘抃,甘抃荐之。上召见,赐钱,以为此人甚廉而贤,除监察御史。
先生闻黄文叔之死,颇伤之,云:「观其文字议论,是一个白直响快底人,想是懊闷死了。言不行,谏不听,要去又不得去,也是闷人!」因言:「蜀中今年煞死了系名色人,如胡子远吴挺,都是有气骨底。吴是得力边将。」
近世士大夫忧国忘家,每言及国家辄感愤慷慨者,惟于赵子直黄文叔见之耳。
赵子直奉命将入蜀,请于先生,曰:「某将入蜀,蜀中亦无事可理会。意欲请于朝,得沿淮差遣,庶可理会屯田。」曰:「出于朝廷之意,犹恐不得终其事。若自请以行,则下梢或有小事请乞不行,便难出手。如举荐小吏而不从其荐,或按劾小吏而不从其劾,或求钱米以补阙之而不从其所求,这如何做?」
赵子直政事都琐碎,看见都闷人。曾向择之云:「朱丈想得不喜某政事。」可知是不喜。
或言赵子直多疑。先生曰:「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?」鲁可几曰:「只是见不破尔。」
赵子直要分门编奏议,先生曰:「只是逐人编好。」因论旧编精义,逐人编,自始终有意。今一齐节去,更拆散了,不见其全意矣。
赵子直亦可谓忠臣,然以宗社之大计言之,亦有未是处,不知何以见先帝!
一日独侍坐,先生忽颦蹙云:「赵丞相谪命似出胡纮。」问:「胡纮不知曾识他否?」曰:「旧亦识之。此人颇记得文字,莆阳之政亦好,但见朋友多说其很愎。」某曰:「丞相前日之事,做得都是否?」曰:「也有些不是处。」问所以不是处。曰:「公他日当自见之。」先生又曰:「一时正人皆已出去,今全无一好人在朝!」某曰:「郑溥之当时草赵丞相罢相词固好。以某观之,当时不做便乞出,尤为奇特。」曰:「也不必如此。但是后来既迁之后,便出亦自好。它却不合不肯出,所以可疑。若说教他不做便出,亦无此典故。」某曰:「且如富郑公缴遂国夫人之封,以前亦何曾有此?自富公既做,后遂为例。」先生微笑而不答。某又问:「丞相秉轴,首召先生入经筵。命下,士子相庆,以为太平可致。忽然一日报罢,莫不惶惑。窃议者云:『先生请早晚入讲筵,人主将不能堪,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侧。』」曰:「早晚入讲筵,非某之请,是自来如此。然某当时便教久在讲筵,恐亦无益。一日虽是两番入讲筵,文字分明,一一解注,亦只讲过而已,看来亦只是文具。」枅。
或曰:「今世士大夫不诡随者,亦有五六人。」曰:「此辈在向时,本是阘茸人,不比数底。但今则上面一项真个好人尽屏除了,故这一辈稍稍能不变,便称好人。其实班固九品之中,方是中下品人。若中中以上,不复有矣。」先生因问:「某人如何?」或曰:「也靠不得。」曰:「然。见他写书来,皆不可晓。顷在某处得书来,说学问又如何,资质又如何,读书不长进又如何。某答之云:『不须如何,说话不济事。若资质弱,便放教刚;若过刚,便放教稍柔些;若懒,便放教勤。读论语,便彻头彻尾理会论语;读孟子,便彻头彻尾理会孟子;其它书皆然。此等事,本不用问人,问人只是杭唐日子,不济事。只须低着头去做。若做底,自是不消问人。』这番又得他书,亦不可晓。」或曰:「终是他于利欲之场打不透。欲过这边,却舍彼不得;欲倒向那边,又畏朋友之议。又缘顷被某人抬奖得太正如个舡阁在沙岸上,要上又不得,要下又推不动。」曰:「然。无一番大水来泛将去,这舡终不动。要之,只是心不勇之故。某尝叹息天下有些英雄人,都被释氏引将去,甚害事!且如昔日老南和尚,他后生行脚时,已有六七十人随着他参请。于天下丛林尊宿,无不遍谒,无有可其意者。只闻石霜楚圆之名,不曾得去,遂特地去访他。及到石霜,颇闻其有不可人意处。南大不乐,徘徊山下数日,不肯去见。后来又思量既到此,须一见而决。如是又数日,不得已,随众入室。揭帘欲入,又舍不得拜他。如是者三,遂奋然曰:『为人有疑不决,终非丈夫?』遂揭帘径入。才交谈,便被石霜降下。他这般人立志勇决如此。观其三四揭帘而不肯入,他定不肯诡随人也。广录云:「世上有一种人,心下自不分明,只是怕人道不会,不肯问人。昔老南去参慈明时,已有人随他了。它欲入慈明室,数次欲揭帘入去,又休。末后乃云:『有疑不决,终非大丈夫!』遂入其室。」某尝说,怪不得今日士大夫,是他心里无可作做,无可思量,『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』,自然是只随利欲走。间有务记诵为词章者,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,所以个个如此。只缘无所用心,故如此。前辈多有得于佛学,当利害祸福之际而不变者。盖佛氏勇猛精进、清净坚固之说,犹足以使人淡泊有守,不为外物所移也。若记览词章之学,这般伎俩,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窠窟动!」或曰:「某人读书,只是摘奇巧为文章以求富贵耳。」曰:「恁地工夫,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,定无气魄,所以他文字皆困苦。某小年见上一辈,未说如何,个个有气魄,敢担当做事。而今人个个都恁地衰,无气魄,也是气运使然。而今秀才便有些气魄,少年被做那时文,都销磨尽了。所以都无精采,做事不成。」
彪居正德美记得无限史记,只是不肯说,只要说一般无巴鼻底道理。在南岳说:「『温故而知新』,不是今人所说之故新。故者,性也;新者,心也。温性而知心,故可以为人师。」其说道理如此,然口哓哓不肯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