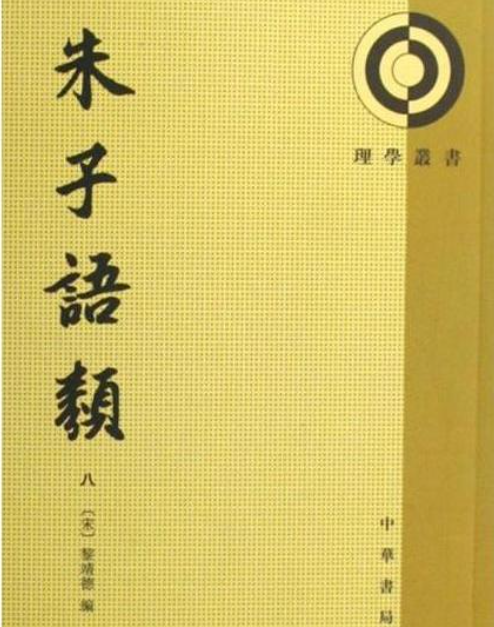论语十七
泰伯篇
泰伯其可谓至德章
泰伯得称「至德」,为人所不能为。
问「泰伯可谓至德」。曰:「这是于『民无得而称焉』处见,人都不去看这一句。如此,则夫子只说『至德』一句便了,何必更下此六个字?公更仔细去看这一句,煞有意思。」义刚言:「夫子称泰伯以至德,称文王亦以至德,称武王则曰未尽善。若以文王比武王,则文王为至德;若以泰伯比文王,则泰伯为至德。文王『三分天下有其二』,比泰伯已是不得全这一心了。」曰:「是如此。」义刚又言:「泰伯若居武王时,牧野之师也自不容已。盖天命人心,到这里无转侧处了。」曰:「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。圣人之制行不同:『或远或近,或去或不去。』虽是说他心只是一般,然也有做得不同处。」范益之问:「文王如何?」曰:「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。纵使文王做时,也须做得较详缓。武王做得大故粗暴。当时纣既投火了,武王又却亲自去斫他头来枭起。若文王,恐不肯恁地。这也难说。武王当时做得也有未尽处,所以东坡说他不是圣人,虽说得太过,然毕竟是有未尽处。」义刚曰:「武王既杀了纣,有微子贤,可立,何不立之?而必自立,何也?」先生不答,但蹙眉,再言:「这事也难说!」
陈仲亨说「至德」,引义刚前所论者为疑。曰:「也不是不做这事,但他做得较雍容和缓,不似武王样暴。泰伯则是不做底,若是泰伯当纣时,他也只是为诸侯。太王翦商,自是他周人恁地说。若无此事,他岂肯自诬其祖!左氏分明说『泰伯不从』,不知不从甚么事。东坡言:『「三分天下有其二」,文王只是不管他。』此说也好。但文王不是无思量,观他戡黎、伐崇之类时,也显然是在经营。」又曰:「公刘时得一上做得盛,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时,又衰了。太王又旋来那岐山下做起家计。但岐山下却亦是商经理不到处,亦是空地。当时邠也只是一片荒凉之地,所以他去那里辑理起来。」
问:「泰伯之让,知文王将有天下而让之乎,抑知太王欲传之季历而让之乎?」曰:「泰伯之意,却不是如此。只见太王有翦商之志,自是不合他意;且度见自家做不得此事,便掉了去。左传谓『泰伯不从,是以不嗣』,不从,即是不从太王翦商事耳。泰伯既去,其势只传之季历,而季历传之文王。泰伯初来思量,正是相反;至周得天下,又都是相成就处。看周内有泰伯虞仲,外有伯夷叔齐,皆是一般所见,不欲去图商。」
问:「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,而王季又有圣子,故让去。」曰:「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。」或问:「太王有翦商之志,果如此否?」曰:「诗里分明说『实始翦商』。」又问:「恐诗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。」曰:「若推本说,不应下『实始翦商』。看左氏云『泰伯不从,是以不嗣』,这甚分明。这事也难说。他无所据,只是将孔子称『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』,是与称文王一般。泰伯文王伯夷叔齐是『行一不义,杀一不辜,而得天下不为』底道理。太王汤武是吊民伐罪,为天下除残贼底道理。常也是道理合如此,变也是道理合如此,其实只是一般。」又问:「尧之让舜,禹之传子,汤放桀,武王伐纣,周公诛管蔡,何故圣人所遇都如此?」先生笑曰:「后世将圣人做模范,却都如此差异,信如公问。然所遇之变如此,到圣人处之皆恁地,所以为圣人,故曰『遭变事而不失其常』。孔子曰:『可与适道,未可与立;可与立,未可与权。』公且就平平正正处看。」
吴伯英问:「泰伯知太王欲传位季历,故断发文身,逃之荆蛮,示不复用,固足以遂其所志,其如父子之情何?」曰:「到此却顾恤不得。父子君臣,一也。太王见商政日衰,知其不久,是以有翦商之意,亦至公之心也。至于泰伯,则惟知君臣之义,截然不可犯也,是以不从。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,圣人未常说一边不是,亦可见矣。或曰:『断发文身,乃仲雍也,泰伯则端委以治吴。』然吴之子孙,皆仲雍之后,泰伯盖无后也。」
问泰伯事。曰:「这事便是难。若论有德者兴,无德者亡,则天命已去,人心已离,便当有革命之事。毕竟人之大伦,圣人且要守得这个。看圣人反复叹咏泰伯及文王事,而于武又曰『未尽善』,皆是微意。」
因说泰伯让,曰:「今人纔有些子让,便惟恐人之不知。」
伯丰问:「集注云:『太王因有翦商之志。』恐鲁颂之说,只是推本之辞,今遂据以为说,可否?」曰:「诗中分明如此说。」又问:「如此则太王为有心于图商也。」曰:「此是难说。书亦云:『太王肇基王迹。』」又问:「太王方为狄人所侵,不得已而迁岐,当时国势甚弱,如何便有意于取天下?」曰:「观其初迁底规模,便自不同。规模才立,便张大。如文王伐崇,伐密,气象亦可见。然文王犹服事商,所以为至德。」集注。
「泰伯」章所引「其心即夷齐之心,而事之难处有甚焉者」,不是说逊国事。自是说夷齐谏武王,不信便休,无甚利害。若泰伯不从翦商之志,却是一家内事,与谏武王不同,所以谓之难处,非说逊国事也。集注说亦未分晓耳。
「泰伯之心,即伯夷叩马之心;太王之心,即武王孟津之心,二者『道并行而不相悖』。然圣人称泰伯为至德,谓武为未尽善,亦自有抑盖泰伯夷齐之事,天地之常经,而太王武王之事,古今之通义,但其间不无些子高下。若如苏氏用三五百字骂武王非圣人,则非矣。于此二者中,须见得『道并行而不悖』处,乃善。」因问:「泰伯与夷齐心同,而谓『事之难处有甚焉者』,何也?」曰:「夷齐处君臣间,道不合则去。泰伯处父子之际,又不可露形迹,只得不分不明且去。某书谓太王有疾,泰伯采药不返,疑此时去也。」
问:「泰伯让天下,与伯夷叔齐让国,其事相类。何故夫子一许其得仁,一许其至德,二者岂有优劣耶?」曰:「亦不必如此。泰伯初未尝无仁,夷齐初未尝无德。」
问:「『三以天下让』,程言:『不立,一也;逃之,二也;文身,三也。』不知是否?」曰:「据前辈说,亦难考。他当时或有此三节,亦未可知。但古人辞,必至再三,想此只是固让。」集注。
恭而无礼章
礼,只是理,只是看合当恁地。若不合恭后,却必要去恭,则必劳。若合当谨后,谨则不葸;若合当勇后,勇则不乱。若不当直后,却须要直,如证羊之类,便是绞。
问:「『故旧不遗,则民不偷』,盖人皆有此仁义之心。笃于亲,是仁之所发,故我笃于亲,则民兴仁;笃故旧,是义之发,故不遗故旧,则民兴义。是如此否?」曰:「看『不偷』字,则又似仁,大概皆是厚底意思。不遗故旧固是厚,这不偷也是厚,却难把做义说。」
问:「『君子笃于亲』,与恭、谨、勇、直处意自别。横渠说如何?」曰:「横渠这说,且与存在,某未敢决以为定。若做一章说,就横渠说得似好。他就大处理会,便知得品节如此。」问:「横渠说『知所先后』,先处是『笃于亲』与『故旧不遗』。」曰:「然。」问:「他却将恭慎等处,入在后段说,是如何?」曰:「就他说,人能笃于亲与不遗故旧,他大处自能笃厚如此,节文处必不至大段有失。他合当恭而恭,必不至于劳;谨慎,必不至于畏缩;勇直处,亦不至于失若不知先后,要做便做,更不问有六亲眷属,便是证父攘羊之事。」集注。
郑齐卿问集注举横渠说之意。曰:「他要合下面意,所以如此说。盖有礼与笃亲、不遗故旧在先,则不葸、不劳、不乱、不绞,与兴仁、不偷之效在后耳。要之,合分为二章。」又问:「直而无礼则绞。」曰:「绞如绳两头绞得紧,都不宽舒,则有证父攘羊之事矣。」
张子之说,谓先且笃于亲,不遗故旧,此其大者,则恭、慎、勇、直不至难用力。此说固好,但不若吴氏分作两边说为是。
问:「横渠『知所先后』之说,其有所节文之谓否?」曰:「横渠意是如此:『笃于亲』,『不遗故旧』,是当先者;恭慎之类却是后。」
曾子有疾谓门弟子章
正卿问「曾子启手足」章。曰:「曾子奉持遗体,无时不戒慎恐惧,直至启手足之时,方得自免。这个身己,直是顷刻不可不戒慎恐惧。如所谓孝,非止是寻常奉事而已。当念虑之微有毫发差错,便是悖理伤道,便是不孝。只看一日之间,内而思虑,外而应接事物,是多多少少!这个心略不点检,便差失了。看世间是多少事,至危者无如人之心。所以曾子常常恁地『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』。」
问曾子战兢。曰:「此只是戒慎恐惧,常恐失之。君子未死之前,此心常恐保不得,便见得人心至危。且说世间甚物事似人心危!且如一日之间,内而思虑,外而应接,千变万化,札眼中便走失了!札眼中便有千里万里之远!所谓『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』。只理会这个道理分晓,自不危。『惟精惟一』,便是守在这里;『允执厥中』,便是行将去。」
曾子曰:「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。」此乃敬之法。此心不存,则常昏矣。今人有昏睡者,遇身有痛痒,则蹶然而醒。盖心所不能已,则自不至于忘。中庸戒慎恐惧,皆敬之意。
时举读问目。曰:「依旧有过高伤巧之病,切须放令平实。曾子启手足是如此说,固好。但就他保身上面看,自极有意思也。」
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章
问:「『正颜色,斯近信矣。』此其形见于颜色者如此之正,则其中之不妄可知,亦可谓信实矣,而只曰近信,何故?」曰:「圣贤说话也宽,也怕有未便恁地底。」
问:「『正颜色,斯近信。』如何是近于信?」曰:「近,是其中有这信,与行处不违背。多有人见于颜色自恁地,而中却不恁地者。如『色厉而内荏』,『色取仁而行违』,皆是外面有许多模样,所存却不然,便与信远了。只将不好底对看,便见。」
「出辞气,斯远鄙倍」,是「修辞立其诚」意思。
「出辞气」,人人如此,工夫却在下面。如「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」,人人皆然,工夫却在「勿」字上。
毅父问「远暴慢」章。曰:「此章『暴慢、鄙倍』等字,须要与他看。暴,是粗厉;慢,是放肆。盖人之容貌少得和平,不暴则慢。暴是刚者之过,慢是宽柔者之鄙是凡浅,倍是背理。今人之议论有见得虽无甚差错,只是浅近者,此是鄙。又有说得甚高,而实背于理者,此是倍。不可不辨也。」
仲蔚说「动容貌」章。曰:「暴慢底是大故粗。『斯近信矣』,这须是里面正后,颜色自恁地正,方是近信。若是『色取仁而行违』,则不是信了。倍,只是倍于理。出辞气时,须要看得道理如何后方出,则不倍于理。」问:「三者也似只一般样。」曰:「是各就那事上说。」又问:「要恁地,不知如何做工夫?」曰:「只是自去持守。」池录作「只是随事去持守。」
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一章,是成就处。以下总论。
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,此三句说得太快,大概是养成意思较多。赐。
陈寅伯问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。曰:「且只看那『所贵』二字。莫非道也。如笾豆之事,亦是道,但非所贵。君子所贵,只在此三者。『动容貌,斯远暴慢矣』,『斯』字来得甚紧。动容貌,便须远暴慢;正颜色,便须近信;出辞气,便须远鄙倍。人之容貌,只有一个暴慢,虽浅深不同,暴慢则一。如人很戾,固是暴;稍不温恭,亦是暴。如人倨肆,固是慢;稍或怠缓,亦是慢。正颜色而不近信,却是色庄。信,实也。正颜色,便须近实。鄙,便是说一样卑底说话。倍,是逆理。辞气只有此二病。」因曰:「不易。孟敬子当时焉得如此好!」或云:「想曾子病亟,门人多在傍者。」曰:「恐是如此。」因说:「看文字,须是熟后,到自然脱落处方是。某初看此,都安排不成。按得东头西头起,按得前面后面起。到熟后,全不费力。要紧处却在那『斯』字、『矣』字这般闲字上。此一段,程门只有尹和靖看得出。孔子曰:『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!』若熟后,真个使人说!今之学者,只是不深好后不得其味,只是不得其味后不深好。」
敬之问此章。曰:「『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』,是题目一句。下面要得动容貌,便能远暴慢;要得正颜色,便近信;出辞气,便远鄙倍。要此,须是从前做工夫。」
问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。曰:「此言君子存养之至,然后能如此。一出辞气,便自能远鄙倍;一动容貌,便自能远暴慢;正颜色,便自能近信,所以为贵。若学者,则虽未能如此,当思所以如此。然此亦只是说效验。若作工夫,则在此句之外。」
杨问:「『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』,若未至此,如何用工?」曰:「只是就容貌辞色之间用工,更无别法。但上面临时可做,下面临时做不得,须是熟后能如此。初间未熟时,虽蜀本淳录作「须」字。是动容貌,到熟后自然远暴慢;虽是正颜色,到熟后自然近信;虽是出辞气,到熟后自然远鄙倍。」淳录此下云:「辞是言语,气是声音,出是从这里出去,三者是我身上事要得如此。笾豆虽是末,亦道之所在,不可不谨。然此则有司之事,我亦只理会身上事。」
「『动容貌,斯远暴慢;正颜色,斯近信;出辞气,斯远鄙倍。』须要会理如何得动容貌,便会远暴慢;正颜色,便会近信;出辞气,便会远鄙倍。须知得曾子如此说,不是到动容貌,正颜色,出辞气时,方自会恁地。须知得工夫在未动容貌,未正颜色,未出辞气之前。」又云:「正颜色,若要相似说,合当着得个远虚伪矣。动、出都说自然,惟正字,却似方整顿底意思。盖缘是正颜色亦有假做恁地,内实不然者。若容貌之动,辞气之出,却容伪不得。」
问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。曰:「看来三者只有『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』。」又问:「要之,三者以涵养为主。」曰:「涵养便是。只这三者,便是涵养地头。但动容貌、远暴慢便是,不远暴慢,便不是;颜色近信便是,不近信,便不是。」
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。或云:「须是工夫持久,方能得如此否?」曰:「不得。人之资禀各不同,资质好者,纔知得便把得定,不改变;资质迟慢者,须大段着力做工夫,方得。」因举徐仲车从胡安定学。一日,头容少偏,安定忽厉声云:「头容直!」徐因思,不独头容直,心亦要直,自此不敢有邪心。又举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,其师见之,厉声叱之曰:「恁地无脊梁骨!」小南闻之耸然,自此终身不靠倚坐。「这样人,都是资质美,所以一拨便转,终身不为。」
问:「所谓暴慢、鄙倍,皆是指在我者言否?」曰:「然。」曰:「所以动容貌而暴慢自远者,工夫皆在先欤?」曰:「此只大纲言人合如此。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,然即今亦须随事省察,不令间断。」
叔京来问「所贵乎道者三」。因云:「正、动、出时,也要整齐,平时也要整齐。」方云:「乃是敬贯动静。」曰:「恁头底人,言语无不贯动静者。」
或问:「远与近意义如何?」曰:「曾子临终,何尝又安排下这字如此?但圣贤言语自如此耳。不须推寻不要紧处。」
「动容貌,斯远暴慢」,是为得人好;「正颜色,斯近信」,是颜色实;「出辞气,斯远鄙倍」,是出得言语是。动、正、出三字,皆是轻说君子所贵于此者,皆平日功夫所至,非临事所能捏合。笾豆之事,虽亦莫非道之所在,然须先择切己者为之。如有关雎麟趾之意,便可行周官法度;又如尽得「皇极」之五事,便有庶征之应。以「笾豆之事」告孟敬子,必其所为有以烦碎为务者。
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,言道之所贵者,有此三事,便对了。道之所贱者,笾豆之事,非不是道,乃道之末耳。如「动容貌,正颜色,出辞气」,须是平日先有此等工夫,方如此效验。「动容貌,斯远暴慢矣」,须只做一句读。「斯」字,只是自然意思。杨龟山解此一句,引曾子修容阍人避之事,却是他人恭慢,全说不着。
问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至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」。曰:「以道言之,则不可谓此为道,彼为非道。然而所贵在此,则所贱在彼矣;其本在此,则其末在彼矣。」
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,乃是切于身者。若笾豆之事,特有司所职掌耳。今人于制度文为一一致察,未为不是;然却于大体上欠阙,则是弃本而求末也。
问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。曰:「学者观此一段,须看他两节,先看所贵乎道者是如何,这个是所贵所重者;至于一笾一豆,皆是理,但这个事自有人管,我且理会个大者。且如今人讲明制度名器,皆是当然,非不是学,但是于自己身上大处却不曾理会,何贵于学!」先生因言:「近来学者多务高远,不自近处着工夫。」有对者曰:「近来学者诚有好高之弊。有问伊川:『如何是道?』伊川曰:『行处是。』又问明道:『如何是道?』明道令于父子君臣兄弟上求。诸先生言如此,初不曾有高远之说。」曰:「明道之说固如此。然父子兄弟君臣之间,各有一个当然之理,是道也。」谦之。
义刚说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一章毕,因曰:「道虽无所不在,而君子所重则止此三事而已。这也见得穷理则不当有小大之分,行己则不能无缓急先后之序。」先生曰:「这样处也难说。圣贤也只大概说在这里。而今说不可无先后之序,固是;但只拣得几件去做,那小底都不照管,也不得。」义刚因言:「义刚便是也疑,以为古人事事致谨,如所谓『克勤小物』,岂是尽视为小而不管?」曰:「这但是说此三事为最重耳。若是其它,也不是不管。只是说人于身己上事都不照管,却只去理会那笾豆等小事,便不得。言这个有有司在,但责之有司便得。若全不理会,将见以笾为豆,以豆为笾,都无理会了。田子方谓魏文侯曰:『君明乐官,不明乐音。』此说固好。但某思之,人君若不晓得那乐,却如何知得那人可任不可任!这也须晓得,方解去任那人,方不被他谩。如笾豆之类,若不晓,如何解任那有司!若笾里盛有汁底物事,豆里盛干底物事,自是不得,也须着晓始得,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。」
舜功问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。曰:「动容貌,则能远暴慢;正颜色,则能近信;出辞气,则能远鄙倍。所贵者在此。至于笾豆之事,虽亦道之所寓,然自有人管了,君子只修身而已。盖常人容貌不暴则多慢,颜色易得近色庄,言语易得鄙而倍理。前人爱说动字、出字、正字上有工夫,看得来不消如此。」
正卿问:「正颜色之正字,独重于动与出字,何如?」曰:「前辈多就动、正、出三字上说,一向都将三字重了。若从今说,便三字都轻,却不可于中自分两样。某所以不以彼说为然者,缘看文势不恁地。『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』,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贵者为说,故云道之所以可贵者有三事焉,故下数其所以可贵之实如此。若礼文器数,自有官守,非在所当先而可贵者。旧说所以未安者,且看世上人虽有动容貌者,而便辟足恭,不能远暴慢;虽有正颜色者,而『色取仁而行违』,多是虚伪不能近信;虽有出辞气者,而巧言饰辞,不能远鄙倍,这便未见得道之所以可贵矣。道之所以可贵者,惟是动容貌,自然便会远暴慢;正颜色,自然便会近信;出辞气,自然便会远鄙倍,此所以贵乎道者此也。」又云:「三句最是『正颜色,斯近信』见得分明。」
或问:「『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』,如何?」曰:「『动容貌,正颜色,出辞气』,前辈不合将做用工处,此只是涵养已成效验处。『暴慢、鄙倍、近信』,皆是自己分内事。惟近信不好理会。盖君子才正颜色,自有个诚实底道理,异乎『色取仁而行违』者也。所谓『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』,道虽无乎不在,然此三者乃修身之效,为政之本,故可贵。容貌,是举一身而言;颜色,乃见于面颜者而言。」又问:「三者固是效验处,然不知于何处用工?」曰:「只平日涵养便是。」
某病中思量,曾子当初告孟敬子「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」,只说出三事。曾子当时有多少好话,到急处都说不办,只撮出三项如此。这三项是最紧要底。若说这三事上更做得工夫,上面又大段长进。便不长进,也做得个圣贤坯模,虽不中不远矣。
「所贵乎道者三」。礼亦是道。但道中所贵此三者在身上。李先生云:「曾子临死,空洞中只余此念。」
或讲「所贵乎道者三」。曰:「不必如此说得巧。曾子临死时话说,必不暇如此委曲安排。」
「注云:『暴,粗厉也。』何谓粗厉?」曰:「粗,不精细也。」集注。
问:「先生旧解,以三者为『修身之验,为政之本,非其平日庄敬诚实存省之功积之有素,则不能也』,专是做效验说。如此,则『动、正、出』三字,只是闲字。后来改本以『验』为『要』,『非其』以下,改为『学者所当操存省察,而不可有造次顷刻之违者也』。如此,则工夫却在『动、正、出』三字上,如上蔡之说,而不可以效验言矣。某疑『动、正、出』三字,不可以为做工夫字。『正』字尚可说。『动』字、『出』字,岂可以为工夫耶?」曰:「这三字虽不是做工夫底字,然便是做工夫处。正如着衣吃饭,其着其吃,虽不是做工夫,然便是做工夫处。此意所争,只是丝发之间,要人自认得。旧来解以为效验,语似有病,故改从今说。盖若专以为平日庄敬持养,方能如此,则不成未庄敬持养底人,便不要『远暴慢,近信,远鄙倍』!便是旧说『效验』字太深,有病。」
「『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』以下三节,是要得恁地,须是平日庄敬工夫到此,方能恁地。若临时做工夫,也不解恁地。」植因问:「明道『动容周旋中礼,正颜色则不妄,出辞气,正由中出』,又仍是以三句上半截是工夫,下半截是功效。」曰:「不是。所以恁地,也是平日庄敬工夫。」
问:「动也,正也,出也,不知是心要得如此?还是自然发见气象?」曰:「上蔡诸人皆道此是做工夫处。看来只当作成效说,涵养庄敬得如此。工夫已在前了,此是效验。动容貌,若非涵养有素,安能便免暴慢!正颜色,非庄敬有素,安能便近信!信是信实,表里如一。色,有『色厉而内荏』者,色庄也;『色取仁而行违者』。苟不近实,安能表里如一乎!」问:「正者,是着力之辞否?」曰:「亦着力不得。若不到近实处,正其颜色,但见作伪而已。」问:「『远』之字义如何?」曰:「远,便是无复有这气象。」问:「正颜色既是功效到此,则宜自然而信,却言『近信』,何也?」曰:「这也是对上『远』字说。」集义。
问:「『君子道者三』章,谢氏就『正、动、出』上用工。窃谓此三句,其要紧处皆是『斯』字上。盖斯者,便自然如此也。才动容貌,便自然远暴慢;非平昔涵养之熟,何以至此!此三句乃以效言,非指用功地步也。」曰:「是如此。」柄。
舜功问:「『动容貌』,如何『远暴慢』?」曰:「人之容貌,非暴则慢,得中者极难,须是远此,方可。此一段,上蔡说亦多有未是处。」问:「『其言也善』,何必曾子?天下自有一等人临死言善。通老云:『圣贤临死不乱。』」曰:「圣贤岂可以不乱言?曾子到此愈极分明,易箦事可见。然此三句,亦是由中以出,不是向外斗撰成得。」
「动容貌,出辞」先生云:「只伊川语解平平说,未有如此张筋弩力意思。」谓上蔡语。
曾子以能问于不能章
陈仲亨说「以能问于不能」章。曰:「想是颜子自觉得有未能处,但不比常人十事晓得九事,那一事便不肯问人。观颜子『无伐善,无施劳』,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。」又问:「『君子人与』,是才德出众之君子?」曰:「『托六尺之孤,寄百里之命』,才者能之;『临大节而不可夺』,则非有德者不能也。」
举问「犯而不校」。曰:「不是着意去容他,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。盖其所存者广大,故人有小小触犯处,自不觉得,何暇与之校耶!」
「不校」,是不与人比校强弱胜负,道我胜你负,我强你弱。如上言「以能问于不能」之类,皆是不与人校也。
子善问:「『犯而不校』,恐是且点检自家,不暇问他人。」曰:「不是如此。是他力量大,见有犯者,如蚊虫、虱子一般,何足与校!如『汪汪万顷之波,澄之不清,挠之不浊』。」亚夫问:「黄叔度是何样底人?」曰:「当时亦是众人扛得如此,看来也只是笃厚深远底人。若是有所见,亦须说出来。且如颜子是一个不说话底人,有个孔子说他好。若孟子,无人印证他,他自发出许多言语。岂有自孔孟之后至东汉黄叔度时,已是五六百年,若是有所见,亦须发明出来,安得言论风旨全无闻!」亚夫云:「郭林宗亦主张他。」曰:「林宗何足凭!且如元德秀在唐时也非细。及就文粹上看,他文章乃是说佛。」南升。
「颜子犯而不校」,是成德事。孟子「三自反」,却有着力处。学者莫若且理会自反,却见得自家长短。若遽学不校,却恐儱侗,都无是非曲直,下梢于自己分却恐无益。
或问:「『犯而不校。』若常持不校之心,如何?」曰:「此只看一个公私大小,故伊川云:『有当校者,顺理而已。』」
大丈夫当容人,勿为人所容。「颜子犯而不校」。
问:「如此,已是无我了。集注曰『非几于无我者不能』,何也?」曰:「圣人则全是无我;颜子却但是不以我去压人,却尚有个人与我相对在。圣人和人我都无。」
问:「『几于无我』,『几』字,莫只是就『从事』一句可见耶?抑并前五句皆可见耶?『犯而不校』,则亦未能无校,此可见非圣人事矣。」曰:「颜子正在着力、未着力之间,非但此处可见,只就『从事』上看,便分明,不须更说无校也。」
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章
圣人言语自浑全温厚。曾子便恁地刚,有孟子气象。如「可以托六尺之孤,可以寄百里之命,临大节而不可夺」等语,见得曾子直是峻厉!
问:「『可以托六尺之孤』云云,不知可见得伊周事否?」曰:「伊周亦未足道此。只说有才志气节如此,亦可为君子之事。」又问:「下此一等,如平勃之入北军,迎代王,霍将军之拥昭,立宣,可当此否?」曰:「这也随人做。圣人做出,是圣人事业;贤人做出,是贤人事业;中人以上,是中人以上事业。这通上下而言。『君子人与?君子人也。』上是疑词。如平勃当时,这处也未见得。若诛诸吕不成,不知果能死节否?古人这处怕亦是幸然如此。如药杀许后事,光后来知,却含胡似这般所在,解『临大节而不夺』否,恐未必然。」因言:「今世人多道东汉名节无补于事。某谓三代而下,惟东汉人才,大义根于其心,不顾利害,生死不变其节,自是可保。未说公卿大臣,且如当时郡守惩治宦官之亲党,虽前者既为所治,而来者复蹈其迹,诛殛窜戮,项背相望,略无所创。今士大夫顾惜畏惧,何望其如此!平居暇日琢磨淬厉,缓急之际,尚不免于退缩。况游谈聚议,习为软熟,卒然有警,何以得其仗节死义乎!大抵不顾义理,只计较利害,皆奴婢之态,殊可鄙厌!」又曰:「东坡议论虽不能无偏颇,其气节直是有高人处。如说孔北海曹操,使人凛凛有生气!」又曰:「如前代多有幸而不败者。如谢安,桓温入朝,已自无策,从其废立,九锡已成,但故为延迁以俟其死。不幸而病小苏,则将何以处之!拥重兵上流而下,何以当之!于此看,谢安果可当仗节死义之资乎?」寓曰:「坦之倒持手板,而安从容闲雅,似亦有执者。」曰:「世间自有一般心胆大底人。如废海西公时,他又不能拒,废也得,不废也得,大节在那里!」砥录略。
正卿问:「『可以托六尺之孤』,至『君子人也』,此本是兼才节说,然紧要处却在节操上。」曰:「不然。三句都是一般说。须是才节兼全,方谓之君子。若无其才而徒有其节,虽死何益。如受人托孤之责,自家虽无欺之之心,却被别人欺了,也是自家不了事,不能受人之托矣。如受人百里之寄,自家虽无窃之之心,却被别人窃了,也是自家不了事,不能受人之寄矣。自家徒能『临大节而不可夺』,却不能了得他事,虽能死,也只是个枉死汉!济得甚事!如晋之荀息是也。所谓君子者,岂是敛手束脚底村人耶!故伊川说:『君子者,才德出众之名。』孔子曰:『君子不器。』既曰君子,须是事事理会得方可。若但有节而无才,也唤做好人,只是不济得事。」
正卿问「托六尺之孤」一章。曰:「『百里之命』,只是命令之『命』。『托六尺之孤』,谓辅幼主;『寄百里之命』,谓摄国政。」曰:「如霍光当得此三句否?」曰:「霍光亦当得上面两句,至如许后之事,则大节已夺了。」曰:「托孤寄命,虽资质高者亦可及;『临大节而不可夺』,非学问至者恐不能。」曰:「资质高底,也都做得;学问到底,也都做得。大抵是上两句易,下一句难。譬如说『有猷,有为,有守』,托孤寄命是有猷、有为,『临大节而不可夺』,却是有守。霍光虽有为,有猷矣,只是无所守。」
「托六尺之孤,寄百里之命」,是才;「临大节不可夺」,是德。如霍光可谓有才,然其毒许后事,便以爱夺了。燕慕容恪是慕容暐之霍光,其辅幼主也好。然知慕容评当去而不去之,遂以乱国,此也未是。惟孔明能之。赐。夔孙同。
问「君子人与?君子人也」。曰:「所谓君子,这三句都是不可少底。若论文势,却似『临大节不可夺』一句为重。然而须是有上面『托六尺之孤,寄百里之命』,却『临大节而不可夺』,方足以为君子。此所以有结语也。」
问:「『可以托六尺之孤,可以寄百里之命』,又能『临大节而不可夺』,方可谓之君子。是如此看否?」曰:「固是。」又问:「若徒能『临大节不可夺』,而才力短浅,做事不得,如荀息之徒,仅能死节而不能止难,要亦不可谓之君子。」曰:「也是不可谓之君子。」
问:「胡文定以荀息为『可以托六尺之孤,寄百里之命,临大节而不可夺』,如何?」曰:「荀息便是不可以托孤寄命了。」问:「圣人书荀息,与孔父仇牧同辞,何也?」曰:「圣人也且是要存得个君臣大义。」
问「君子才德出众之名」。曰:「有德而有才,方见于用。如有德而无才,则不能为用,亦何足为君子。」「君子人与」章伊川说。
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
「『弘毅』二字,『弘』虽是宽广,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宽容看了,便不得。且如『执德不弘』之『弘』,便见此『弘』字,谓为人有许多道理。及至学来,下梢却做得狭窄了,便是不弘。盖缘只以己为是,凡他人之言,便做说得天花乱坠,我亦不信,依旧只执己是,可见其狭小,何缘得弘?须是不可先以别人为不是,凡他人之善,皆有以受之。集众善之谓弘。」伯丰问:「是『宽以居之』否?」曰:「然。如『人能弘道』,却是以弘为开廓,『弘』字却是作用。」专论「弘」。
问「『弘毅』之『弘』」。曰:「弘是宽广,事事着得:道理也着得:事物也着得;事物逆来也着得,顺来也着得;富贵也着得,贫贱也着得。看甚么物事来,掉在里面,都不见形影了。」
「弘」字,只将「隘」字看,便见得。如看文字相似,只执一说,见众说皆不复取,便是不弘。若是弘底人,便包容众说,又非是于中无所可否。包容之中,又为判别,此便是弘。
弘,有耐意。如有一行之善,便道我善了,更不要进;能些小好事,便以为只如此足矣,更不向前去,皆是不弘之故。如此其小,安能担当得重任!
所谓「弘」者,不但是放令公平宽大,容受得人,须是容受得许多众理。若执着一见,便自以为是,他说更入不得,便是滞于一隅,如何得弘。须是容受轧捺得众理,方得。」谦之。
恭甫问:「弘是心之体?毅是心之力?」曰:「心体是多少大!大而天地之理,纔要思量,便都在这里。若是世上浅心弘己底人,有一两件事,便着不得。」
「士不可以不弘毅」。这曾子一个人,只恁地,他肚里却着得无限。今人微有所得,欣然自以为得。
毅,是立脚处坚忍强厉,担负得去底意。以下兼论「毅」。
敬之问:「弘,是容受得众理;毅,是胜得个重任。」曰:「弘乃能胜得重任,毅便是能担得远去。弘而不毅,虽胜得任,却恐去前面倒了。」
问:「弘是宽容之义否?」曰:「固是。但不是宽容人,乃宽容得义理耳。弘字,曾子以任重言之。人之狭隘者,只守得一义一理,便自足。既滞一隅,却如何能任重。必能容纳吞受得众理,方是弘也。」
仲蔚问「弘毅」。曰:「弘,不只是有度量、能容物之谓,正是『执德不弘』之『弘』。是无所不容,心里无足时,不说我德已如此便住。如无底之谷,掷一物于中,无有穷尽。若有满足之心,便不是弘。毅,是忍耐持守,着力去做。」
问「弘毅」。曰:「弘是宽广耐事,事事都着得:道理也着得多,人物也着得多。若着得这一个,着不得那一个,便不是弘。且如有两人相争,须是宽着心都容得,始得。若便分别一人是,一人非,便不得。或两人都是,或两人都非,或是者非,非者是,皆不可知。道理自是个大底物事,无所不备,无所不包。若小着心,如何承载得起。弘了却要毅。弘则都包得在里面了,不成只恁地宽里面又要分别是非,有规矩,始得。若只恁地弘,便没倒断了。『任重』,是担子重,非如任天下之『任』。」又曰:「若纔小着这心,便容两个不得。心里只着得一个,这两个便相挂碍在这里,道理也只着得一说,事事都只着得一边。」
问:「曾子弘毅处,不知为学工夫久,方会恁地,或合下工夫便着恁地?」曰:「便要恁地。若不弘不毅,难为立脚。」问:「人之资禀偏驳,如何便要得恁地?」曰:「既知不弘不毅,便警醒令弘毅,如何讨道理教他莫恁地!弘毅处固未见得,若不弘不毅处,亦易见。不弘,便急迫狭隘,不容物,只安于卑陋。不毅,便倾东倒西,既知此道理当恁地,既不能行,又不能守;知得道理不当恁地,却又不能割舍。除却不弘,便是弘;除了不毅,便是毅。这处亦须是见得道理分晓,磊磊落落。这个都由我处置,要弘便弘,要毅便毅。如多财善贾,须多蓄得在这里,看我要买也得,要卖也得。若只有十文钱在这里,如何处置得去!」又曰:「圣人言语自浑全温厚,曾子便有圭角。如『士不可以不弘毅』,如『可以托六尺之孤』云云,见得曾子直是恁地刚硬!孟子气象大抵如此。」淳录云:「徐问:『弘毅是为学工夫久方能如此?抑合下便当如此?』曰:『便要弘毅,皆不可一日无。』曰:『人之资禀有偏,何以便能如此?』曰:『只知得如此,便警觉那不如此,更那里别寻讨方法去医治他!弘毅处亦难见,不弘不毅却易见。不弘,便浅迫,便窄狭,不容物,便安于卑陋。不毅,便倒东坠西,见道理合当如此,又不能行,不能守;见道理不当如此,又不能舍,不能去。只除了不弘,便是弘;除了不毅,便是毅。非别讨一弘毅来。然亦须是见道理极分晓,磊磊落落在这里,无遁惰病痛来;便都由自家处置,要弘便弘,要毅便毅。如多财善贾,都蓄在这里,要买便买,要卖便卖。若止有十文钱在此,则如何处置得!」砥录云:「居父问:『士不可不弘毅。学者合下当便弘毅,将德盛业成而后至此?』曰:『合下便当弘毅,不可一日无也。』又问:『如何得弘毅?』曰:『但只去其不弘不毅,便自然弘毅。弘毅虽难见,自家不弘不毅处却易见,常要检点。若卑狭浅隘,不能容物,安于固陋,便是不弘。不毅处病痛更多。知理所当为而不为,知不善之不可为而不去,便是不毅。』又曰:『孔子所言,自浑全温厚,如曾子所言,便有孟子气象。』」
问「士不可以不弘毅」。曰:「弘是事事着得,如进学者要弘,接物也要弘,事事要弘。若不弘,只是见得这一边,不见那一边,便是不弘。只得些了便自足,便不弘。毅却是发处勇猛,行得来强忍,是他发用处。」问:「后面只说『仁以为己任』,是只成就这个仁否?」曰:「然。许多道理也只是这个仁,人也只要成就这个仁,须是担当得去。」又问:「『死而后已』,是不休歇否?」曰:「然。若不毅,则未死已前,便有时倒了。直到死方住。」又曰:「古人下字各不同。如『刚、毅、勇、猛』等字,虽是相似,其义训各微不同,如适间说『推』与『充』相似。」
「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!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!」须是认得个仁,又将身体验之,方真个知得这担子重,真个是难。世间有两种:有一种全不知者,固全无摸索处;又有一种知得仁之道如此大,而不肯以身任之者。今自家全不曾担着,如何知得他重与不重。所以学不贵徒说,须要实去验而行之,方知。
「士不可以不弘毅」,毅者,有守之意。又云:「曾子之学,大抵如孟子之勇。观此弘毅之说,与夫『临大节不可夺』,与孟子『彼以其富,我以吾仁』之说,则其勇可知。若不勇,如何主张得圣道住!如论语载曾子之言先一章云,『以能问于不能』,则见曾子弘处;又言『临大节不可夺』,则见他毅处。若孟子只得他刚处,却少弘大底气象。」
弘而不毅,如近世龟山之学者,其流与世之常人无以异。毅而不弘,如胡氏门人,都恁地撑肠拄肚,少间都没顿着处。
弘,宽广也,是事要得宽阔。毅,强忍也,如云「扰而毅」,是驯扰而却毅,强而有守底意思。「弘」字,如今讲学,须大着个心,是者从之,不是者也且宽心去究。而今人才得一善,便说道自家底是了,别人底都不是,便是以先入为主了;虽有至善,无由见得。如「执德不弘」,须是自家要弘,始得。若容民蓄众底事,也是弘,但是外面事。而今人说「弘」字,多做容字说了,则这「弘」字里面无用工处。可以此意推之。又云:「弘下开阔周遍。」集注。
程子说「弘」字曰「宽广」,最说得好。毅是尽耐得,工夫不急迫。如做一件,今日做未得,又且耐明日做。
问:「毅训『强忍』。粗而言之,是硬担当着做将去否?杨氏作力行说,正此意,但说得不猛厉明白,若不足以形容『毅』字气象。至程子所谓『弘而无毅,则无规矩而难立』,其说固不可易。第恐『毅』字训义,非可以有规矩言之,如何?」曰:「毅有忍耐意思。程子所云无规矩,是说目今;难立,是说后来。」
「士不可以不弘毅」。先生举程先生语曰:「重担子,须是硬着脊梁骨,方担荷得去!」
兴于诗章
或问「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」。曰:「『兴于诗』,便是个小底;『立于礼,成于乐』,便是个大底。『兴于诗』,初间只是因他感发兴起得来,到成处,却是自然后恁地。」又曰:「古人自小时习乐,诵诗,学舞,不是到后来方始学诗,学礼,学乐。如云:『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』,非是初学有许多次第,乃是到后来方能如此;不是说用工夫次第,乃是得效次第如此。」又曰:「到得『成于乐』,是甚次第,几与理为一。看有甚放僻邪侈,一齐都涤荡得尽,不留些子。『兴于诗』,是初感发这些善端起来;到『成于乐』,是刮来刮去,凡有毫发不善,都荡涤得尽了,这是甚气象!」又曰:「后世去古既远,礼乐荡然,所谓『成于乐』者,固不可得。然看得来只是读书理会道理,只管将来涵泳,到浃洽贯通熟处,亦有此意思。」致道云:「读孟子熟,尽有此意。」曰:「也是。只是孟子较感发得粗,其它书都是如此。」贺孙因云:「如大学传『知止』章及『齐家』章引许多诗语,涵泳得熟,诚有不自已处。」
亚夫问此章。曰:「诗、礼、乐,初学时都已学了。至得力时,却有次第。乐者,能动荡人之血气,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着不得,便纯是天理,此所谓『成于乐』。譬如人之服药,初时一向服了,服之既久,则耳聪目明,各自得力。此兴诗、立礼、成乐所以有先后也。」
古人学乐,只是收敛身心,令入规矩,使心细而不粗,久久自然养得和乐出来。又曰:「诗、礼、乐,古人学时,本一齐去学了;到成就得力处,却有先后。然『成于乐』,又见无所用其力。」
「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。」圣人做出这一件物事来,使学者闻之,自然欢喜,情愿上这一条路去,四方八面撺掇他去这路上行。
敬之问:「『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』,觉得和悦之意多。」曰:「先王教人之法,以乐官为学校之长,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这里。」
正卿说「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」。曰:「到得『成于乐』,自不消恁地浅说。『成于乐』是大段极」
只是这一心,更无他说。「兴于诗」,兴此心也;「立于礼」,立此心也;「成于乐」,成此心也。今公读诗,是兴起得个甚么?
或问「成于乐」。曰:「乐有五音六律,能通畅人心。今之乐虽与古异,若无此音律,则不得以为乐矣。」力行因举乐记云:「耳目聪明,血气和平。」曰:「须看所以聪明、和平如何,不可只如此说」
「成于乐」。曰:「而今作俗乐聒人,也聒得人动。况先王之乐,中正平和,想得足以感动人!」
问:「『立于礼』,礼尚可依礼经服行。诗、乐皆废,不知兴诗成乐,何以致之。」曰:「岂特诗、乐无!礼也无。今只有义理在,且就义理上讲究。如分别得那是非邪正,到感慨处,必能兴起其善心,惩创其恶志,便是『兴于诗』之功。涵养德性,无斯须不和不乐,直恁地和平,便是『成于乐』之功。如礼,古人这身都只在礼之中,都不由得自家。今既无之,只得硬做些规矩,自恁地收拾。如诗,须待人去歌诵。至礼与乐,自称定在那里,只得自去做。荀子言:『礼乐法而不说。』更无可说,只得就他法之而已。荀子此语甚好。」又问:「『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』,与此相表里否?」曰:「也不争多,此却有游艺一脚子。」淳录云:「徐问:『「立于礼」,犹可用力。诗今难晓,乐又无,何以兴成乎?』曰:『今既无此家具,只有理义在,只得就理义上讲究。如分别是非到感慨处,有以兴起其善心,惩创其恶志,便是「兴于诗」之功也。涵养和顺,无斯须不和不乐,恁地和平,便是「成于乐」之功也。如礼,今亦无,只是便做些规矩,自恁地收敛。古人此身终日都在礼之中,不由自家。古人「兴于诗」,犹有言语以讽诵。礼,全无说话,只是恁地做去。乐,更无说话,只是声音节奏,使人闻之自然和平。故荀子曰:「礼乐法而不说。」』曰:『此章与「志于道」相表里否?』曰:『彼是言德性道理,此是言事业功夫。此却是「游于艺」脚子。』」道夫录云:「居父问:『「立于礼」犹可用力。诗、乐既废,不知今何由兴成之?』曰:『既无此家具,也只得以义理养其心。若精别义理,使有以感发其善心,惩创其恶志,便是「兴于诗」。涵养从容,无斯须不和不乐,便是「成于乐」。今礼亦不似古人完具,且只得自存个规矩,收敛身心。古人终日只在礼中,欲少自由,亦不可得。』又曰:『诗犹有言语可讽诵。至于礼,只得夹定做去。乐,只是使他声音节奏自然和平,更无说话。荀子又云:「礼乐法而不说。」只有法,更无说也。』或问:『此章与「志道、据德、依仁、游艺」如何?』曰:『不然。彼就德性上说,此就工夫上说,只是游艺一脚意思。』」
「兴于诗」,此三句上一字,谓成功而言也,非如『志于道』四句上一字,以用功而言也。
仲蔚问:「『兴于诗』与『游于艺』,先后不同,如何?」曰:「『兴、立、成』,是言其成;『志、据、依、游』,是言其用功处。夔孙录云:「『志、据、依』,是用力处;『兴、立、成』,是成效处。」但诗较感发人,故在先。礼则难执守,这须常常执守始得。乐则如太史公所谓『动荡血气,流通精神』者,所以涵养前所得也。」问:「『消融渣滓』如何?」曰:「渣滓是他勉强用力,不出于自然,而不安于为之之意,闻乐则可以融化了。然乐,今却不可得而闻矣。」
子寿言:「论语所谓『兴于诗』。又云:『诗,可以兴。』盖诗者,古人所以咏歌情性,当时人一歌咏其言,便能了其义,故善心可以兴起。今人须加训诂,方理会得,又失其歌咏之律,如何一去看着,便能兴起善意?以今观之,不若熟理会论语,方能兴起善意也。」
问:「注言『乐有五声十二律』云云,『以至于义精仁熟,而自和顺于道德』,不知声音节奏之末,如何便能使『义精仁熟,和顺于道德』?」曰:「人以五声十二律为乐之末,淳录云:「不可谓乐之末。」若不是五声十二律,如何见得这乐?便是无乐了。淳录云:「周旋揖逊,不可谓礼之末。若不是周旋揖逊,则为无礼矣,何以见得礼?」五声十二律,皆有自然之和古乐不可见,要之声律今亦难见。然今之歌曲,亦有所谓五声十二律,方做得曲,亦似古乐一般。如弹琴亦然。只他底是邪,古乐是正,所以不同。」又问:「五声十二律,作者非一人,不知如何能和顺道德?」曰:「如金石丝竹,匏土革木,虽是有许多,却打成一片。清浊高下,长短大小,更唱迭和,皆相应,浑成一片,有自然底和气,淳录云:「所以听之自能『义精仁熟,和顺于道德』。乐于歌舞,不是各自为节奏。乐只是此一节奏,歌亦是此一节奏,舞亦是此一节奏。」不是各自为节奏。歌者,歌此而已;舞者,舞此而已。所以听之可以和顺道德者,须是先有兴诗、立礼工夫,然后用乐以成之。」问:「古者『十有三年学乐诵诗,二十而冠,始学礼』,与这处不同,如何?」曰:「这处是大学终身之所得。如十岁学幼仪,十三学乐、诵诗,从小时皆学一番了,做个骨子在这里。到后来方得他力。礼,小时所学,只是学事亲事长之节,乃礼之小者。年到二十,所学乃是朝廷、宗庙之礼,乃礼之大者。到『立于礼』,始得礼之力。乐,小时亦学了。到『成于乐』时,始得乐之力。不是大时方去学。诗,却是初间便得力,说善说恶却易晓,可以劝,可以戒。礼只捉住在这里,乐便难精。淳录云:「直是工夫至到,方能有成。」诗有言语可读,礼有节文可守。乐是他人作,与我有甚相关?如人唱曲好底,凡有闻者,人人皆道好。乐虽作于彼,而听者自然竦动感发,故能义精仁熟,而和顺道德。舜命夔曲乐,『教冑子:直而温,宽而栗,刚而无虐,简而无傲』,定要教他恁地。至其教之之具,又却在于『诗言志,歌永言,声依永,律和声』处。五声十二律不可谓乐之末,犹揖逊周旋,不可谓礼之末。若不揖逊周旋,又如何见得礼在那里!」又问:「成于乐处,古人之学有可证者否?」曰:「不必恁地支离。这处只理会如何是『兴于诗』,如何是『立于礼』,如何是『成于乐』。律吕虽有十二,用时只用七个,自黄锺下生至姑洗,便住了。若更要插一个,便拗了。如今之作乐,亦只用七个。如边头写不成字者,即是古之声律。若更添一声,便不成乐。」集注。
问:「注云『乐有五声十二律,更唱迭和』,恐是迭为宾主否?」曰:「书所谓『声依永,律和声』,盖人声自有高下,圣人制五声以括之。宫声洪浊,其次为商;羽声轻清,其次为征;清浊洪纤之中为角,此五声之别,以括人声之高下。圣人又制十二律以节五声,故五声中又各有高下,每声又分十二等。谓如以黄锺为宫,则是太簇为商,姑洗为角,林锺为征,南吕为羽。还至无射为宫,便是黄锺为商,太簇为角,中吕为征,林锺为羽。然而无射之律只长四寸六七分,而黄锺长九寸,太簇长八寸,林锺长六寸,则宫声概下面商角羽三声不故有所谓四清声,夹锺、大吕、黄锺、太簇是也。盖用其半数,谓如黄锺九寸只用四寸半,余三律亦然。如此,则宫声可以概之,其声和矣。不然,则其声不得其和。看来十二律皆有清声,只说四者,意其取数之甚多者言之,余少者尚庶几焉。某人取其半数为子声,谓宫律之短,余则用子声。某人又破其说曰:『子声非古有也。』然而不用子声,则如何得其和?毕竟须着用子声。想古人亦然,但无可考耳。而今俗乐多用夹锺为黄锺之宫,盖向上去声愈清故也。」又云:「今之琴,第六七弦是清声。如第一二弦以黄锺为宫,太簇为商,则第六七弦即是黄锺、太簇之清,盖只用两清声故也。」
正淳问:「谢氏谓『乐则存养其善心,使义精仁熟,自和顺于道德,遗其音而专论其意』,如何?」曰:「『乐』字内自括五音六律了。若无五音六律,以何为乐?」集义。
民可使由之章
问「民可使由之」。曰:「所谓『虽是他自有底,却是圣人使之由』。如『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』,『教以人伦:父子有亲,君臣有义,夫妇有别,长幼有序,朋友有信』,岂不是『使之由』。」问:「不可使知之」。曰:「不是愚黔首,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。吕氏谓『知之未至,适所以启机心而生惑志』,说得是。」问:「此不知与『百姓日用不知』同否?」曰:「彼是自不知,此是不能使之知。」
植云:「民可使之仰事俯育,而不可使之知其父子之道为天性;可使之奔走服役,而不可使之知其君臣之义为当然。」及诸友举毕,先生云:「今晚五人看得都无甚走作。」
或问「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」。曰:「圣人只使得人孝,足矣,使得人弟,足矣,却无缘又上门逐个与他解说所以当孝者是如何,所以当弟者是如何,自是无缘得如此。顷年张子韶之论,以为:『当事亲,便当体认取那事亲者是何物,方识所谓仁;当事兄,便当体认取那事兄者是何物,方识所谓义。』某说,若如此,则前面方推这心去事亲,随手又便去背后寻摸取这个仁;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,随手又便着一心去寻摸取这个义,是二心矣。禅家便是如此,其为说曰:『立地便要你究得,恁地便要你究得。』他所以撑眉弩眼,使棒使喝,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当识认取,所以谓之禅机。若必欲使民知之,少间便有这般病。某尝举子韶之说以问李先生曰:『当事亲,便要体认取个仁;当事兄,便要体认取个义。如此,则事亲事兄却是没紧要底事,且姑借此来体认取个仁义耳。』李先生笑曰:『不易,公看得好。』」或问:「上蔡爱说个『觉』字,便是有此病了。」曰:「然。张子韶初间便是上蔡之说,只是后来又展上蔡之说,说得来放肆无收杀了。」或曰:「南轩初间也有以觉训仁之病。」曰:「大概都是自上蔡处来。」又曰:「吕氏解『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』,云:『「不可使知」,非以愚民,盖知之不至,适以起机心而生惑志也。』此说亦自好。所谓机心,便是张子韶与禅机之说。方纔做这事,便又使此心去体认,少间便启人机心。只是圣人说此语时,却未有此意在。向姑举之或问,不欲附集注。」或曰:「王介甫以为『不可使知』,尽圣人愚民之意。」曰:「申韩庄老之说,便是此意,以为圣人置这许多仁义礼乐,都是殃考人。淮南子有一段说,武王问太公曰:『寡人伐纣,天下谓臣杀主,下伐上。吾恐用兵不休,争斗不已,为之奈何?』太公善王之问,教之以繁文滋礼,以持天下,如为三年之丧,令类不蓄,厚葬久丧,以亶音丹。其家。其意大概说,使人行三年之丧,庶几生子少,免得人多为乱之意;厚葬久丧,可以破产,免得人富以启乱之意。都是这般无稽之语!」
「民可使由之」一章,旧取杨氏说,亦未精审。此章之义,自与盘、诰之意不同。商盘只说迁都,周诰只言代商,此不可不与百姓说令分晓。况只是就事上说,闻者亦易晓解。若义理之精微,则如何说得他晓!
好勇疾贫章
「好勇疾贫」,固是作乱。不仁之人,不能容之,亦必致乱,如东汉之党锢。
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
「周公之才之美」,此是为有才而无德者言。但此一段曲折,自有数般意思,骄者必有吝,吝者必有骄。非只是吝于财,凡吝于事,吝于为善,皆是。且以吝财言之,人之所以要吝者,只缘我散与人,使他人富与我一般,则无可矜夸于人,所以吝。某尝见两人,只是无紧要闲事,也抵死不肯说与人。只缘他要说自会,以是骄夸人,故如此。因曾亲见人如此,遂晓得这「骄吝」两字,只是相匹配得在,故相靠得在。池录作:「相比配,相靠在这里。」
骄吝,是挟其所有,以夸其所无。挟其所有,是吝;夸其所无,是骄。而今有一样人,会得底不肯与人说,又却将来骄人。
正卿问:「骄如何生于吝?」曰:「骄却是枝叶发露处,吝却是根本藏蓄处。且以浅近易见者言之:如说道理,这自是世上公共底物事,合当大家说出来。世上自有一般人,自恁地吝惜,不肯说与人。这意思是如何?他只怕人都识了,却没诧异,所以吝惜在此。独有自家会,别人都不会,自家便骄得他,便欺得他。如货财也是公共底物事,合使便着使。若只恁地吝惜,合使不使,只怕自家无了,别人却有,无可强得人,所以吝惜在此。独是自家有,别人无,自家便做大,便欺得他。」又云:「为是要骄人,所以吝。」
或问「骄吝」。曰:「骄是傲于外,吝是靳惜于中。骄者,吝之所发;吝者,骄之所藏。」
某昨见一个人,学得些子道理,便都不肯向人说。其初只是吝,积蓄得这个物事在肚里无柰何,只见我做大,便要陵人,只此是骄。
圣人只是平说云,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骄吝,也连得才美功业坏了,况无周公之才美而骄吝者乎!甚言骄吝之不可也。至于程子云:「有周公之德,则自无骄吝」,与某所说骄吝相为根本枝叶,此又是发余意。解者先说得正意分晓,然后却说此,方得。
先生云:「一学者来问:『伊川云:「骄是气盈,吝是气歉。」歉则不盈,盈则不歉,如何却云「使骄且吝」?』试商量看。」伯丰对曰:「盈是加于人处,歉是存于己者。粗而喻之,如勇于为非,则怯所迁善;明于责人,则暗于恕己,同是一个病根。」先生曰:「如人晓些文义,吝惜不肯与人说,便是要去骄人。非骄,无所用其吝;非吝,则无以为骄。」
问:「『骄气盈,吝气歉。』气之盈歉如何?」曰:「骄与吝是一般病,只隔一膜。骄是放出底吝,吝是不放出底骄。正如人病寒热,攻注上则头目痛,攻注下则腰腹痛。热发出外似骄,寒包缩在内似吝。」因举显道克己诗:「试于清夜深思省,剖破藩篱即大家!」问:「当如何去此病?」曰:「此有甚法?只莫骄莫吝,便是剖破藩篱也。觉其为非,从源头处正。我要不行,便不行;要坐,便还我坐,莫非由我,更求甚方法!」
集注云:「骄吝虽不同,而其势常相因。」先生云:「孔子之意未必如此。某见近来有一种人如此,其说又有所为也。」炎。
「骄者,吝之枝叶;吝者,骄之根本。」某尝见人吝一件物,便有骄意,见得这两字如此。
「吝者,骄之根本;骄者,吝之枝叶」,是吝为主。盖吝其在我,则谓我有你无,便是骄人也。
读「骄吝」一段,云:「亦是相为先后。」
三年学章
问:「『不至于谷』,欲以『至』为『及』字说,谓不暇及于禄,免改为『志』,得否?」曰:「某亦只是疑作『志』,不敢必其然。盖此处解不行,作『志』则略通。不可又就上面撰,便越不好了。」或又引程子说。曰:「说不行,不如莫解;解便不好,如解白为黑一般。」
问:「三年学而不至于谷,是无所为而为学否?」曰:「然。」
笃信好学章
学者须以笃信为先。刘子澄说。
笃信,故能好学;守死,故能善道。惟善道,故能守死;惟好学,故能笃信。每推夫子之言,多如此。
惟笃信,故能好学;惟守死,故能善道。善,如「善吾生,善吾死」之「善」,不坏了道也。然守死生于笃信,善道由于好学。徒笃信而不好学,则所信者或非所信;徒守死而不能推以善其道,则虽死无补。
笃信,须是好学;但要好学,也须是笃信。善道,须是守死,而今若是不能守死,临利害又变了,则亦不能善道。但守死须是善道,若不善道,便知守死也无益,所以人贵乎有学。笃信,方能守死;好学,方能善道。恪录云:「此两句相关,自是四事。惟笃信,故能守死;惟好学,故能善道。」
「危邦不入」,是未仕在外,则不入;「乱邦不居」,是已仕在内,见其纪纲乱,不能从吾之谏,则当去之。
「危邦不入」,旧说谓已在官者,便无可去之义。若是小官,恐亦可去;当责任者,则不容去也。
或问:「危邦固是不可入,但或有见居其国,则当与之同患难,岂复可去?」曰:「然。到此,无可去之理矣。然其失,则在于不能早去。当及其方乱未危之时去之,可也。」
天下无道,譬如天之将夜,虽未甚暗,然此自只向暗去。知其后来必不可支持,故亦须见几而作,可也。
不在其位章
马庄甫问「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」。曰:「此各有分限。田野之人,不得谋朝廷之政。身在此间,只得守此。如县尉,岂可谋他主薄事!纔不守分限,便是犯他疆界。」马曰:「如县尉,可与他县中事否?」曰:「尉,佐官也。既以佐名官,有繁难,只得伴他谋,但不可侵他事权。」
师挚之始章
徐问:「『关雎之乱』,何谓『乐之卒章』?」曰:「自『关关雎鸠』至『锺鼓乐之』,皆是乱。想其初必是已作乐,只无此词。到此处便是乱。」
或问:「『关雎之乱』,乱何以训终?」曰:「既『奏以文』,又『乱以武』。」
「乱曰」者,乱乃乐终之杂声也。乱出国语史记。又曰:「关雎恐是乱声,前面者恐有声而无辞。」
狂而不直章
狂,是好高大,便要做圣贤,宜直;侗,是愚模样,不解一事底人,宜谨愿;悾悾,是拙模样,无能为底人,宜信。有是德,则有是病;有是病,必有是德。有是病而无是德,则天下之弃才也!
问:「『狂而不直』之『狂』,恐不可以进取之『狂』当之。欲目之以轻率,可否?」曰:「此『狂』字固卑下,然亦有进取意思。敢为大言,下梢却无收拾,是也。」
问:「侗者,同也,于物同然一律,无所识别之谓。悾者,空也,空而又空,无一长之实之谓。」先生以为,此亦因旧说,而以字义音训推之,恐或然尔。此类只合大概看,不须苦推究也。
学如不及章
「学如不及,犹恐失之」,如今学者却恁地慢了。譬如捉贼相似,须是着起气力精神,千方百计去赶捉他,如此犹恐不获。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视他,不管他,如何柰得他何!只忺时起来行得三两步,懒时又坐,恁地如何做得事成!
巍巍乎章
看「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」至「禹,吾无间然」四章。先生云:「舜禹与天下不相关,如不曾有这天下相似,都不曾把一毫来奉己。如今人纔富贵,便被他勾惹。此乃为物所役,是自卑了。若舜禹,直是高!首出庶物,高出万物之表,故夫子称其『巍巍』。」又曰:「尧与天为一处,民无能名。所能名者,事业礼乐法度而已。」
正卿问:「舜禹有天下而不与,莫是物各付物,顺天之道否?」曰:「据本文说,只是崇高富贵不入其心,虽有天下而不与耳。巍巍,是至高底意思。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,便觉累其心。今富有天下,一似不曾有相似,岂不是高!」
不与,只是不相干之义。言天下自是天下,我事自是我事,不被那天下来移着。
正淳论:「『不以位为乐』,恐不特舜禹为然。」曰:「不必如此说。如孟子论禹汤一段,不成武王不执中,汤却泄迩、忘远!此章之旨,与后章禹无间然之意同,是各举他身上一件切底事言之。」
因论「舜禹有天下而不与」之义,曰:「此等处,且玩味本文,看他语意所重落向何处。明道说得义理甚闳阔,集注却说得小。然观经文语意落处,却恐集注得之。」
大哉尧之为君章
「惟天为大,惟尧则之」,只是尊尧之词。不必谓独尧能如此,而他圣人不与也。
「惟尧则之」一章。曰:「虽荡荡无能名,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见,又有焕乎之文章可睹。」
「大哉尧之为君!」炎谓:「吴才老书解说驩兜共工辈在尧朝,尧却能容得他,舜便容他不得,可见尧之大处,舜终是不若尧之大。」曰:「吴解亦自有说得好处。舜自侧微而兴,以至即帝位,此三四人终是有不服底意,舜只得行遣。故曰:『四罪而天下咸服。』」炎。
舜有臣五人章
魏问:「集注云『惟唐虞之际乃盈于此』,此恐将『舜有臣五人』一句闲了。」曰:「宁可将上一句存在这里。若从元注说,则是『乱臣十人』,却多于前,于今为盛。却是舜臣五人,不得如后来盛!」
李问「至德」。曰:「『三分天下有其二』,天命人心归之,自可见其德之盛了。然如此而犹且不取,乃见其至处。」
问:「『三分天下有其二,以服事商』,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,将终事纣乎,抑为武王牧野之举乎?」曰:「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。如诗中言:『文王受命,有此武功。既伐于崇,作邑于丰,文王烝哉!』武功皆是文王做来。诗载武王武功却少,但卒其伐功耳。观文王一时气势如此,度必不终竟休了。一似果实,文王待他十分黄熟自落下来,武王却是生拍破一般。」
或问以为:「文王之时,天下已二分服其化。使文王不死,数年天下必尽服。不俟武王征伐,而天下自归之矣。」曰:「自家心如何测度得圣人心!孟子曰:『取之而燕民不悦,则勿取,古之人有行之者,文王是也。』圣人已说底话尚未理会得,何况圣人未做底事,如何测度得!」后再有问者,先生乃曰:「若纣之恶极,文王未死,也只得征伐救民。」
问:「文王受命是如何?」曰:「只是天下归之。」问:「太王翦商,是有此事否?」:「此不可考矣。但据诗云:『至于太王,实始翦商。』左传云:「泰伯不从,是以不嗣。』要之,周自日前积累以来,其势日大;又当商家无道之时,天下趋周,其势自尔。至文王三分有二,以服事殷,孔子乃称其『至德』。若非文王,亦须取了。孔子称『至德』只二人,皆可为而不为者也。周子曰:『天下,势而已矣。势,轻重也。』周家基业日大,其势已重,民又日趋之,其势愈重。此重则彼自轻,势也。」
因说文王事商,曰:「文王但是做得从容不迫,不便去伐商太猛耳。东坡说,文王只是依本分做,诸侯自归之。」或问:「此有所据否?」曰:「这也见未得在。但是文王伐崇、戡黎等事,又自显然。书说『王季勤劳王家』,诗云太王翦商,都是他子孙自说,不成他子孙诬其父祖!春秋分明说『泰伯不从』,是不从甚底事?若泰伯居武王之世,也只是为诸侯。但时措之宜,圣人又有不得已处。横渠云:『商之中世,都弃了西方之地,不管他,所以戎狄复进入中国,太王所以迁于岐。』然岐下也只是个荒凉之地,太王自去立个家计如此。」
问:「文王『三分天下有其二』一段,据本意,只是说文王。或问中载胡氏说,又兼武王而言,以为武王之间以服事商,如何?」曰:「也不消如此说,某也谩载放那里,这个难说。而今都回互个圣人,说得忒好,也不得。如东坡骂武王不是圣人,又也无礼。只是孔子便说得来平,如『武未尽善』。此等处未消理会,且存放那里。」
禹吾无间然章
范益之问:「五峰说『禹无间然矣』章,云是『禹以鲧遭殛死,而不忍享天下之奉』,此说如何?」曰:「圣人自是薄于奉己,而重于宗庙朝廷之事。若只恁地说,则较狭了。后来着知言,也不曾如此说。」
黻,蔽膝也,以韦为之。韦,熟皮也。有虞氏以革,夏后氏以山,「殷火,周龙章」。祭服谓之黻,朝服谓之[韦毕]。左氏:「带裳[韦毕]舄。」